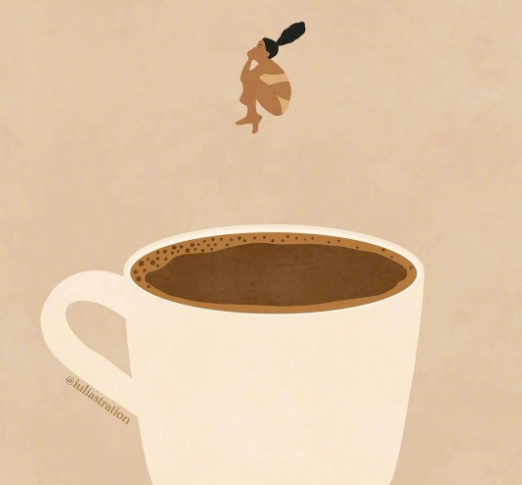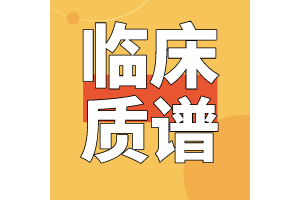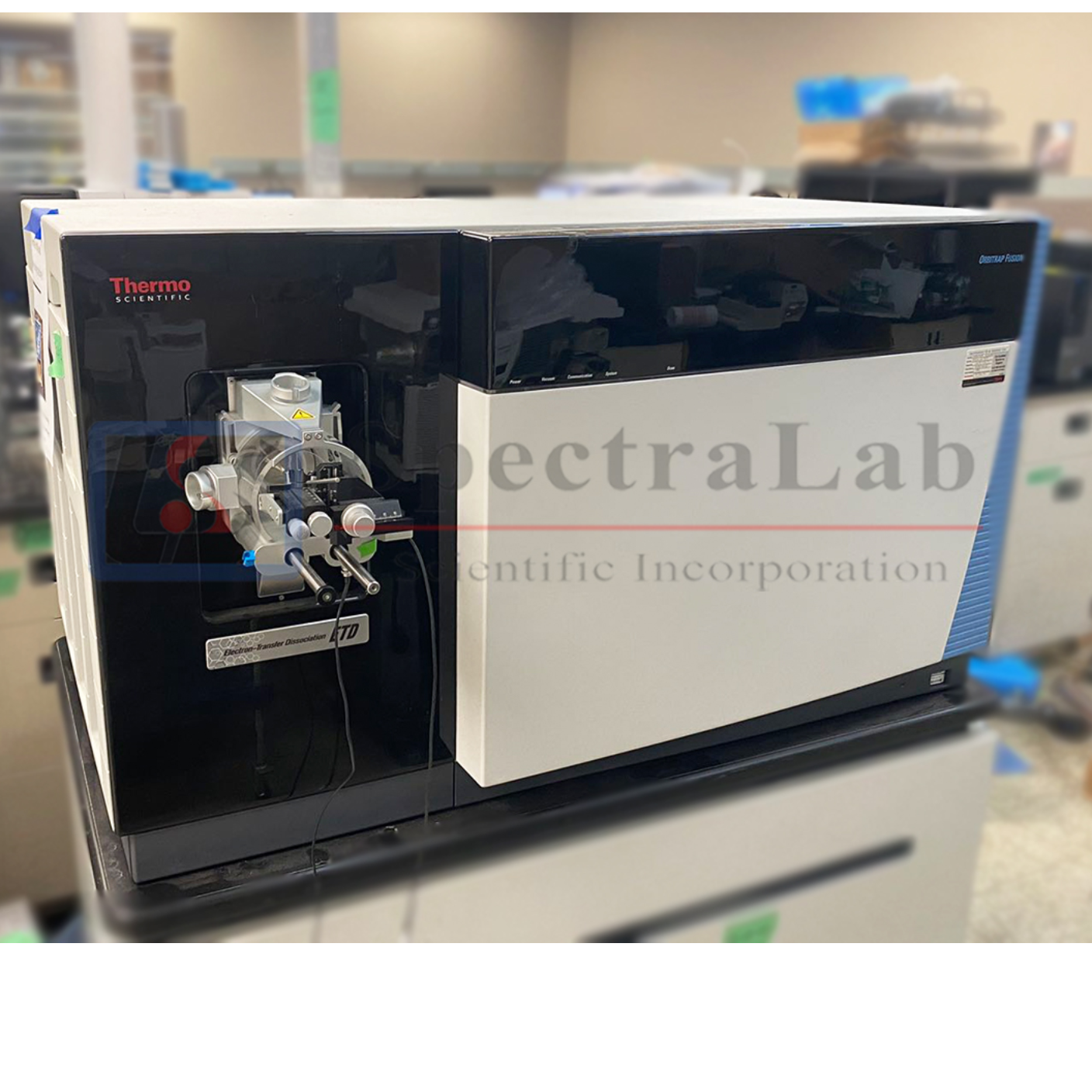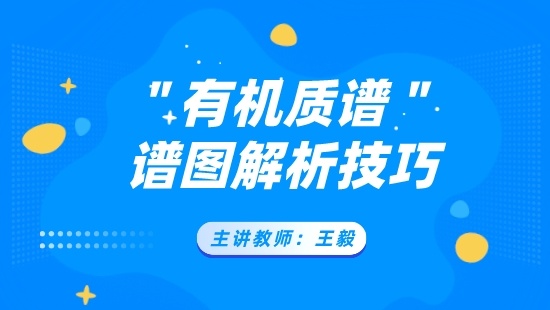涉及质谱法,侵袭性霉菌感染实验室诊断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发布
导读:根据共识文件中的数据显示:质谱对曲霉菌属、毛霉属、淡紫紫孢霉和宛氏拟青霉等均有较高鉴定准确率,有的甚至能达到100%。
共识中提到:侵袭性霉菌感染实验室诊断方法及路径基本一致,包括直接镜检、培养、血清学检测(G试验、GM试验、曲霉IgG抗体测定等)、分子生物学检测(PCR、mNGS),再通过形态学、质谱、分子生物学鉴定具体菌种,进一步进行体外药敏试验并提出治疗建议。
根据共识文件中的数据显示:质谱对曲霉菌属、毛霉属、淡紫紫孢霉和宛氏拟青霉等均有较高鉴定准确率,有的甚至能达到100%。
摘要
侵袭性真菌病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发布了重要文件,呼吁提高对侵袭性真菌病的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以应对侵袭性真菌病对全球造成的威胁。霉菌是侵袭性真菌病的重要病原菌之一,且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临床诊断和治疗面临极大挑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检验医学研究与转化专业委员会、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专业委员会和全国真菌病监测网侵袭性霉菌感染监测项目组组织专家制定该文件,对曲霉菌属、毛霉菌目、镰刀菌属、赛多孢菌属、节荚孢霉属、拟青霉属、暗色霉菌、双相真菌(马尔尼菲篮状菌和荚膜组织胞浆菌)共8种临床重要侵袭性霉菌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及要点形成共识,并对实验室诊断及与临床沟通过程中遇到的六大常见问题形成专家共识,旨在为提升侵袭性霉菌感染的实验室诊断能力提供借鉴和指导。
全球每年真菌感染患者超过3亿,因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死亡的患者超过150万[1,2] ,而我国每年有超过500万人受到IFD的威胁,其中侵袭性霉菌是重要病原菌之一,但临床对侵袭性霉菌感染诊断困难,患者预后较差。国内外IFD相关指南均明确指出,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检测在诊断标准中极为重要 [ 3 , 4 ] 。IFD相关实验室检测,除传统的涂片镜检和培养外,血清学检测如真菌1,3-β-D葡聚糖试验(G试验)、半乳甘露聚糖(galactomannan,GM)试验和曲霉IgG抗体测定等,质谱技术以及分子生物学检测如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等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逐渐得到肯定。但目前我国真菌实验室发展非常不均衡,特别是针对霉菌的实验室检测,不管是临床医生对于检测项目的认知,还是霉菌实验室的检出能力均需进一步提高;同时,不同检测方法的送检时机、检测性能以及结果的正确解读仍面临很多问题。鉴于此,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检验医学研究与转化专业委员会、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专业委员会和全国真菌病监测网侵袭性霉菌感染监测项目组组织我国真菌感染领域内的多学科专家和学者,参考国内外相关指南和最新研究数据,结合多学科专家临床经验共同制定本共识,旨在更好地指导临床医生合理送检真菌相关的实验室检测,提升真菌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助力临床IFD的诊断和治疗。
该共识通过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真菌重点病原体清单”以及全国真菌病监测网最新数据 [ 5 ] ,共筛选出8种临床常见的侵袭性霉菌,即曲霉菌属、毛霉菌目、镰刀菌属、赛多孢菌属、节荚孢霉属、拟青霉属、暗色霉菌、双相真菌(马尔尼菲篮状菌和荚膜组织胞浆菌)。共识第一部分围绕不同霉菌感染建议送检标本类型,实验室检测方法(直接镜检、培养、鉴定、血清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及性能评价,体外药敏试验及治疗建议等要点形成推荐意见;共识第二部分,通过前期问卷调查,筛选出6个霉菌实验室检测最常见问题,并形成专家推荐意见。
本共识适合从事真菌感染相关领域的临床医护人员、实验室技术人员、感染控制人员、科研学者等阅读,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广大同仁交流意见。
一、侵袭性霉菌感染实验室诊断方法及要点
侵袭性霉菌感染实验室诊断方法及路径基本一致,包括直接镜检、培养、血清学检测(G试验、GM试验、曲霉IgG抗体测定等)、分子生物学检测(PCR、mNGS),再通过形态学、质谱、分子生物学鉴定具体菌种,进一步进行体外药敏试验并提出治疗建议( 图1 )。因检测不同霉菌适用的样本类型,以及每种检测方法针对不同霉菌的检测性能及要点有很大差别,故本共识针对8种霉菌感染,建议送检的标本类型以及不同检测方法的操作要点及性能评价分别形成推荐意见。
(一)曲霉菌属
曲霉菌在自然环境中广泛存在,临床最常见的感染类型是侵袭性曲霉病(invasive aspergillosis,IA)和慢性肺曲霉病(chronic pulmonary aspergillosis,CPA),其中IA临床表现和进展速度与患者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 [ 6 , 7 ] 。血液恶性肿瘤、慢性肺病、移植(包括实体器官移植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糖皮质激素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慢性肝病均是IA的危险因素。肺外脏器和组织的曲霉菌感染可为原发感染,也可播散至邻近脏器感染而造成继发感染。除肺部外,鼻窦旁、中枢神经系统、骨骼、皮肤、心脏、眼部及消化系统等部位也可发生曲霉菌感染。临床最常见的曲霉菌为烟曲霉,其次是黄曲霉、黑曲霉、土曲霉和构巢曲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唑类耐药曲霉菌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曲霉菌属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血液、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活检组织、分泌物等,怀疑曲霉菌属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1 。
(二)毛霉菌目
毛霉菌目由55个属250多个种组成。引起人类发病最常见的是根霉属、毛霉属和横梗霉属,其次是根毛霉属和小克银汉霉属等。毛霉菌目可引起皮肤、软组织、肺部、鼻-眶-脑、胃肠部位感染,病死率达40%~80% [ 20 ] 。不同种属可能会导致不同感染部位的复发,如横梗霉属易引起皮肤毛霉病复发,而小克银汉霉属常见于肺部或播散性感染患者。毛霉菌目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血液、痰液、BALF、脓液、分泌物、痂皮或活检组织等,怀疑毛霉菌目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2 。
(三)镰刀菌属
镰刀菌属是一类全球性分布的土壤腐生菌,也是植物病原菌,能引起感染和中毒。镰刀菌属可广泛感染人类,包括浅表感染(如角膜炎和甲真菌病等)、局部侵袭性和播散性感染。局部侵袭性和播散性感染主要发生于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特别是长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或严重T细胞免疫缺陷患者。引起人类感染的镰刀菌种多为茄病镰刀菌复合群、尖孢镰刀菌复合群。此外,摄入镰刀菌毒素污染的食物后可引起中毒。镰刀菌属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角膜刮片、眼内容物、指(趾)甲、皮肤组织、呼吸道标本(痰液、BALF、刷取物、肺穿组织)、关节液、胸腹水、脓液、血液等,怀疑镰刀菌属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3 。
(四)赛多孢菌属
赛多孢菌属呈全球性分布,广泛存在于土壤、污水、腐物等环境中,可定植于囊性纤维化患者呼吸道,是一种重要的条件致病真菌。未经有效治疗,6个月病死率达55% [ 3 ] 。感染类型以创伤后局部感染为主,其次为溺水后感染、免疫功能明显受损后感染及呼吸道内定植感染等 [ 36 ] 。临床主要致病菌种为尖端赛多孢和波氏赛多孢。赛多孢菌属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痰液、BALF、脓液、分泌物、痂皮、血液或活检组织等,怀疑赛多孢菌属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4 。
(五)暗色霉菌
暗色霉菌是一大类可产生黑色素的真菌群体,可分离于多种临床感染标本,根据临床表现及其在组织中的分布特征,暗色霉菌所致常见感染性疾病包括着色芽生菌病、暗色丝孢霉病、孢子丝菌病和足菌肿。暗色霉菌感染常因环境中暗色霉菌经创伤性植入皮肤或皮下组织所致,但肺部感染或播散性感染常为吸入分生孢子所致。虽然暗色霉菌具有相似的生长特征及形态学特征,但部分菌属仍具有明显特征。临床上分离率较高的菌属包括弯孢霉属、离蠕孢属、着色霉属、链格孢霉属、枝孢霉属等。暗色霉菌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组织、脑脊液、脓液、关节腔液、腹水、人工瓣膜、BALF、痰液、骨髓、血液等,怀疑暗色霉菌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5 。
(六)节荚孢霉属
节荚孢霉属包括多育节荚孢霉(原称多育赛多孢)和 L.valparaisensis 2个菌种,其中仅多育节荚孢霉有感染人类的报道。多育节荚孢霉是一种常见的土壤腐生菌,多分布于干旱气候地区。目前,关于多育节荚孢霉的报道以病例报道和小规模队列研究为主,缺乏流行病学数据。感染类型主要是肺部感染、血流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等。虽然多育节荚孢霉感染罕见,但其易发生播散性感染,并且其固有多重耐药表型的播散性感染致死率高达77% [ 44 ] 。节荚孢霉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血液、痰液、BALF、脓液、分泌物或活检组织等,怀疑节荚孢霉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6 。
(七)拟青霉属
拟青霉属中临床常见的菌种包括宛氏拟青霉和淡紫紫孢霉(淡紫拟青霉)。宛氏拟青霉常见感染类型包括肺炎、皮肤和软组织感染、骨髓炎、腹膜炎、真菌血症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常见症状为发热、呼吸困难和咳嗽,其侵袭性感染致死率为16.9% [ 48 ] 。淡紫紫孢霉常引发角膜炎、眼内炎、皮肤感染、肺部感染和真菌血症,疼痛和发热为最常见症状,其引发的感染致死率为45.5% [ 49 ] 。拟青霉属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角膜组织、眼拭子、血液、痰液、BALF、甲屑、鼻窦组织、脓液和皮肤组织等,怀疑拟青霉属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7 。
(八)双相型真菌(马尔尼菲篮状菌和荚膜组织胞浆菌)
马尔尼菲篮状菌,原名马尔尼菲青霉菌,是一种温度依赖性双相型真菌,在我国广西、广东等地,以及东南亚等地流行。目前在世界34个国家、我国21个省/直辖市均有报道。马尔尼菲篮状菌感染好发于免疫低下人群,尤其是CD4+T细胞小于100个/μl的艾滋病患者;在亚洲的艾滋病患者中,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总发病率为3.6%。马尔尼菲篮状菌可侵犯全身各器官,导致播散性感染。但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常被误诊为肺结核、肿瘤,误诊导致的病死率超过85%。
荚膜组织胞浆菌也是双相型真菌,可引起组织胞浆菌病。该菌常见于被蝙蝠粪和鸟粪污染的土壤中,在建筑、洞穴挖掘和接触鸟类处理等活动中吸入分生孢子可致感染。荚膜组织胞浆菌有3个变种,分别为荚膜变种、杜波变种和鼻疽变种。其中荚膜变种分布最广,主要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拉丁美洲;杜波变种主要分布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鼻疽变种主要引起马和狗的感染,但也有少数人类感染病例报道。我国引起发病的主要为荚膜变种,呈地区性分布,多雨潮湿的中南、华南和西南地区感染率较高,而干旱的新疆地区感染率低。马尔尼菲篮状菌和荚膜组织胞浆菌感染诊断可选择的样本类型包括血液、骨髓、体液、痰液、BALF、支刷物、脓液、分泌物、穿刺液(肝、脾、淋巴结)或活检组织等,怀疑马尔尼菲篮状菌和荚膜组织胞浆菌引起的侵袭性真菌感染诊断方法及要点见 表8 。
二、侵袭性霉菌感染实验室诊断常见问题及推荐意见
为更好地提升我国侵袭性霉菌感染实验室诊断能力,解决实验室工作中最常见、最困惑以及与临床交流最多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来自全国76位临床和检验医师的共207个问题。经过归纳分类后,整理出6大类最常见问题,并由专家组形成推荐意见。
(一)霉菌检测阳性,如何判断是污染菌、定植菌还是致病菌
1.直接镜检霉菌阳性,如何判断是污染菌、定植菌还是致病菌?
建议1 直接镜检阳性时,应首先区分标本来自无菌部位还是非无菌部位。无菌部位标本(血液标本除外)直接镜检有特征性菌丝和孢子且与组织病理结果、真菌培养结果相符,可确诊为致病霉菌;非无菌部位标本直接镜检到霉菌,要结合培养结果、血清学检测结果、患者流行病学史和临床感染表现等综合分析。
2.培养霉菌阳性时,如何判断是污染菌、定植菌还是致病菌?
建议2 培养霉菌阳性时,重点关注送检标本类型,直接镜检、组织病理检查与霉菌阳性培养的一致性,以及霉菌致病性、感染部位等。无菌标本如血培养为曲霉菌属或毛霉菌目,污染菌的可能性大;如为镰刀菌属、赛多孢菌属和马尔尼菲篮状菌,可能为致病菌。非无菌标本,视情况而定:2个试管有单一形态真菌生长,真菌镜检同时阳性者提示有临床意义;仅1管生长真菌,生长部位为非接种部位,菌落为霉菌样则可能是污染;培养出的真菌与直接镜检和组织病理学检查表现相符,连续培养阳性,且真菌具备36~37 ℃生长的能力提示有临床意义。
(二)不同检测结果不一致问题
1.临床怀疑真菌感染,实验室相关检测阴性,可从哪些方面与临床沟通?
建议3 分析前应评估标本留取是否规范并适于特定检验项目;分析过程应评估镜检和/或培养方法检测敏感性是否充分、培养条件是否适宜、所选检测项目是否适于检测疑似真菌类型(如G试验不能检测隐球菌和毛霉菌目);分析后过程应结合组织病理学或影像学结果,参考其他感染指标结果(如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分析是否存在导致血清学结果假阴性的因素等。
2.如何解释镜检和/或培养结果与血清学检测(G试验、GM试验)结果不一致?
建议4 鉴于真菌体内增殖及血清标志物出现时间不同,不同感染期血清学与镜检和/或培养结果常不一致。血清学检测方法敏感性常高于传统镜检、培养方法,而单纯培养结果常难区分感染、定植或污染。此外,应考量是否存在导致血清学结果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因素以及宿主免疫功能。
(三)血清学检测相关问题
1.血清学检测常见干扰因素有哪些?
建议5 血清学检测假阳性因素包括药物因素(血液制品如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等)、医疗因素(纤维素膜血液透析)、宿主因素(细菌菌血症)、样本因素(如采血管污染或过度操作)、方法学因素(传统鲎试剂法干扰因素多) [ 65 , 66 ] 等;假阴性因素包括使用抗真菌药物、脂血或黄疸样本 [ 65 , 66 ] 等。实际应用过程中应尽量排除干扰因素的存在,并谨慎评估对结果的干扰影响。
2.如何解释血清G试验与GM试验结果不一致?
建议6 G试验与GM试验检测标志物不同,G试验是泛真菌检测,而GM试验为曲霉菌特异性抗原检测;另外,2种标志物的释放时间和释放量的不同也可能导致二者结果不一致,例如1,3-β-D葡聚糖只有被吞噬细胞吞噬处理后才被释放出来,而GM是表达在曲霉菌细胞壁表面的一种多糖成分,在曲霉菌繁殖生长时由菌丝释放出来。因此,在感染早期,曲霉菌的生长分泌强于死亡消化裂解,可出现GM试验阳性,而G试验未达到阳性水平;粒细胞缺乏患者,不能将1,3-β-D葡聚糖从真菌中释放出来,也可导致二者检测结果不一致。
3.如何解释血清与BALF的GM试验结果不一致?
建议7 二者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不同,可能会导致检测结果的不一致。GM试验对免疫抑制患者IA检测敏感性高,BALF样本敏感性优于血清样本 [ 9 ] 。另外BALF样本采样和处理的标准化问题(灌洗量、回收量、血性、痰性、灌洗技术等)对GM试验结果的影响很大。
(四)mNGS检测相关问题
1.mNGS检测霉菌相比于传统检测方法的优势有哪些?
mNGS检测敏感性高,更适合混合感染病例的病原学检测,多项侵袭性真菌感染的研究表明mNGS检测阳性率高于传统检测,且对免疫缺陷患者和混合感染时较传统检测更具优势 [ 67 , 68 , 69 ] 。外周血可作为深部组织器官真菌感染的mNGS检测样本:侵袭性真菌感染可累及多种组织和器官。当感染部位样本获取困难时,外周血可作为替代样本进行检测。mNGS可作为少见真菌或培养困难真菌的平行检测手段,如毛霉菌目、组织胞浆菌、拟青霉等。
建议8 对免疫功能低下、疑似混合感染、传统检测阴性或疑似少见真菌感染患者,在进行传统微生物学检测的同时留取样本进行mNGS检测。外周血样本检测敏感性低于感染部位样本,因此在不能获得感染部位样本时可进行替代检测,检出真菌应结合临床谨慎评估。
2.mNGS检测有哪些局限性?
真菌的细胞壁相对较厚,mNGS可因破壁效率低而影响核酸提取效率,且检测性能可因真菌类型、临床样本种类及实验流程差异而有所不同。有研究显示IA患者的BALF样本其mNGS检测敏感性低于GM检测 [ 15 ] 。公共数据库中真菌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度低于细菌及病毒,已有的核酸序列质量参差不一,可导致结果假阴性或真菌鉴定准确率降低。对于检出的非常见真菌类型,应进行其他方法的验证,如一代测序或靶向PCR检测。mNGS假阳性较常见,主要原因为湿试验过程引入微生物核酸及生信分析错配,前者更常见。湿试验所致假阳性原因包括样本采集环节、实验室环境背景菌以及样本间污染 [ 70 ] 。
建议9 mNGS假阳性率高于传统微生物学检测,仅mNGS检出真菌不应作为真菌感染的诊断依据,应对检出真菌进行其他方法验证,并需结合临床谨慎评估。与此同时,因真菌结构特点及数据库原因,mNGS可存在假阴性结果,mNGS阴性不应作为排除真菌感染的标准。
3.当临床考虑IFD时,如何解释镜检、培养、血清学检测与mNGS检测结果不一致?
不同方法学的诊断性能存在较大差异。(1)传统微生物学未检出真菌,而mNGS检出:与培养、镜检方法相比,mNGS的敏感性较高,需结合临床考虑检出真菌是否为致病菌,同时应考虑送检其他真菌相关检测以验证mNGS结果。(2)传统微生物学检出真菌,而mNGS未检出:无菌样本培养和/或镜检检出霉菌,应充分考虑致病菌可能,mNGS可因真菌细胞壁较厚、人源背景高等原因造成漏检。
建议10 当临床考虑IFD时,应充分考虑阳性结果检出,结合未检出的检测方法性能特征考虑漏检可能,有条件情况下进行重复检测或重新采集样本检测。
(五)霉菌体外药敏试验相关问题
1.霉菌是否均需常规开展体外药敏试验?
建议11 微生物实验室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尽量开展重要病原真菌的体外药敏试验,为临床用药提供指导,具体用药原则建议由临床相关科室、微生物实验室、药剂科、感控部门共同讨论决定。特别是下列情况,实验室应该开展体外药敏试验:(1)建立致病性霉菌抗菌谱和耐药性监测。(2)使用标准剂量的抗霉菌药物治疗失败的患者。(3)临床上已有临床耐药菌株报道。(4)曾接触过抗真菌类药物或正在接受长期抗真菌治疗的患者。
接受抗真菌治疗的患者发生深度感染、治疗失败的情况下,若无菌部位分离出霉菌菌种为罕见或新出现的菌种,或怀疑特定菌种可能对所使用的抗真菌药物耐药的情况下,应优化患者个体化治疗,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等情况,建议进行体外药敏试验。
2.对无判定折点的药敏结果,如何向临床发送报告?
建议12 如分离出高度疑似或确诊为病原体的霉菌,应尽量向临床提供体外药敏试验结果。药敏试验暂无判定折点的霉菌也需提供体外药敏试验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值。
由于诸多因素,目前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研究所(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欧洲抗微生物药物敏感试验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EUCAST)以及我国对多数霉菌缺乏临床药敏试验判读折点。对已有规范化体外药敏试验方法的霉菌(如曲霉、毛霉、镰刀菌、赛多孢、孢子丝菌、皮肤癣菌等),可按照抗丝状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肉汤稀释法标准(WS/T411-2024) [ 71 ] 向临床提供体外药敏试验MIC值,临床可结合抗真菌药物的血药谷浓度和峰浓度值,选择相应的药物种类和剂量。对于尚无规范化体外药敏试验方法的霉菌(如暗色真菌等),可参考类似菌体外药敏试验方法测定其MIC值,报告临床,并注明体外药敏试验非标准化方法操作,此结果仅供参考。
(六)如何保证侵袭性霉菌实验室检测的生物安全,避免实验室污染?
建议13 霉菌实验室不应与细菌、结核实验室共用,应单独设置;霉菌检测需在Ⅱ级生物安全柜内进行,特别是可疑高致病性病原真菌;紫外线仍然是必备的空气消毒设备;定期使用高锰酸钾或甲醛熏蒸24 h,对空气进行消杀;每天实验完成后用0.5%过氧乙酸或含氯消毒剂(500 mg/L)消毒。如遇操作台被真菌或标本污染,应立即覆盖纸巾,并用含氯消毒液(500 mg/L)消毒20 min。一旦实验室环境或培养箱发生污染,应立即停止实验操作,对实验室或培养箱进行彻底消毒,可用含氯消毒液(500 mg/L)进行表面消毒擦拭,然后进行过氧乙酸或甲醛熏蒸,熏蒸后再进行表面消毒,连续3 d监测实验室或培养箱空气质量和表面染菌量,确认无污染后方可重新启用。
执笔人(按姓氏拼音排序):曹存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杜君洋(侵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范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辜依海(三二〇一医院微生物免疫科),黄晶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检验科),刘亚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王贺(侵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王俊瑞(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徐春晖(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临床检测中心),徐和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曹存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曹俊敏(浙江省中医院检验科),褚云卓(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杜君洋(侵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范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辜依海(三二〇一医院微生物免疫科),郭大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韩崇旭(苏北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胡付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临床微生物室),黄晶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检验科),贾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金炎(山东省立医院检验科),康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李轶(河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梁伟(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林宁(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检验科),刘亚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罗燕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办公室),马筱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逄崇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感染科),王贺(侵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王俊瑞(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王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魏莲花(甘肃省人民医院检验科),肖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徐春晖(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临床检测中心),徐和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许建成(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检验科),徐雪松(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检验科),徐英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喻华(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张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张利侠(陕西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张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检验医学中心),朱镭(山西省儿童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来源于: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热门评论
最新资讯
新闻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