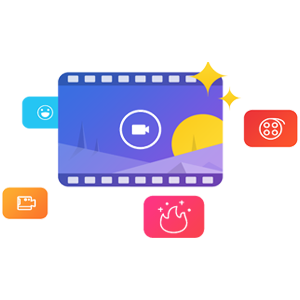

茅茅
第1楼2009/01/24
第二部分
这美妙的园里有一位仙灵,
这伊甸的夏娃,一位美与欢乐的女神,
象上帝主宰宇宙星辰,管理着
不论是醒着或是睡梦中的花朵。
一位姑娘,一位美得惊人的女性,
优美形体内的优美心灵,
规范着也显现于她的仪态和举动,
象海花开放在大海洋中。
她照料花园,从清早直到黄昏,
夜来了,月下天廷的流星
象众多的空中明灯,
欢笑在她脚旁,照耀她离地飞升;
她没有任何人间伴侣,
但是当黎明从她眼上把睡意吻去,
那晕红的脸色,微微发颤的呼吸
却表明她的梦是天堂不是沉睡;
好象有个俊美的精灵,趁着星光灿烂,
为了和她欢会,抛弃了天廷来到人间,
似乎仍在她声旁徘徊、逡巡,
虽然白昼的帷幕隐去了他的形影。
她的脚步仿佛怜悯被残踏的小草;
从她的胸脯起伏中可以听得到,
轻风吹来,带给她欢欣,
风过后,留下炽热的激情。
无论她轻盈的脚步落在哪里,
她飘逸的秀发都要从草地
用轻盈的扫掠把轻微的足迹扫去,
象和煦的急风扫掠过暗绿色的海域。
我不怀疑,那美妙花园的花朵
听到她温柔的脚步声会感到欢乐;
我不怀疑,它们和她晶莹的手指接触,
会感到有一种精神立即在全身流布。
她汲取清冽的溪水,把日光下,
中暑昏迷的花儿浇萨,
又从负载沉重的花盏内,
清除掉雷雨留下的积水;
她用温馨的纤指把它们的头颅扶起,
又用竹竿和柳树皮支持它们的身姿;
如果这些花是她自己的儿女,
她也不能护理得更加温存体恤。
一切害虫、啃嗤花木的蛆,
不洁的东西,不美的形体,
她都给装进一只印度筐笼,
抛弃到远远隔离的荒野林丛。
为了使可怜的被逐昆虫得以疗饥,
筐里还装满了她双手所能采集的
最鲜嫩的野花和青草作为食物,
因为它们虽然为害,本心却也无辜。
但是蜜蜂和生命短促如电的蜉蝣,
喜欢亲吻甜蜜花唇的柔软飞蛾,
全都无害,她就加以收容,
充当身边供她驱使的仆从。
还有羽化前蝶蛹的许多坟墓,
未来的蝴蝶正在那里梦着未来的生活,
她都听任它们留在平滑、黝暗
散发松脂清香的雪松树皮上边
这位最美的人儿从早春起
就这样活动在花园里,
又经过整个迷人的夏季,
未见第一片黄叶——她竟死去!
茅茅
第2楼2009/01/24
第三部分
整整三天,这美妙园中的花朵
就象月亮醒来后的星星,也象
月亮穿过维苏威的浓烟升空以前
贝伊的海面,一片阴暗。
到第四天,那敏感的含羞草,
感觉到了丧葬哀乐的音调,
抬棺者的脚步,沉重而迟缓,
吊丧者的哭泣,深沉而凄惨。
疲惫的声音,沉重的呼吸,
死亡通过时,无声的轻移,
棺材缝隙透出来的气味,
寒冷、阴暗,使人压抑。
阴暗的草和草丛中的花朵,
泪珠闪烁,当送丧的行列走过;
风从它们的叹息感染到哀音,
坐在松林中,以呻吟回答呻吟。
一度美好的花园变得脏臭阴冷,
象具死尸,失去了她——它的灵魂,
起初还恬静,仿佛是在安睡,
后来慢慢变化,终于变为
使人战栗而不是哭泣的一堆。
夏季的急流向秋日行进,
寒霜在晨雾中驰骋。
虽然中午的阳光明媚,
嘲笑着黑夜暗中的劫掠。
玫瑰花瓣象绯红的雪片,
覆盖着下面的草地和苔藓。
百合花垂下头去,象病人垂危,
头颅和皮肤苍白而憔悴。
芳香、艳丽的印度花草,
在饮露为生的族类中最为美妙,
如今却日复一日,叶复一叶,
零落委地,化为寻常污泥。
棕色的黄色的灰色的红色的
和有着死者才有的白色的落叶,
象鬼魂的队列乘干燥的风飞行,
它们的呼啸使飞鸟惊心。
一阵阵疾风把有翅的种子唤醒,
带它们脱离诞生地丑恶的杂草远行,
直到在许多娇美花朵的梗茎上粘附,
又随梗茎的腐烂埋入泥土。
小河里的水中花朵,
也从茎上纷纷凋落,
漩流驱送它们到这到那,
象旋风卷带空中的飞花。
接着大雨倾盆,折断的花茎
弯曲,纠缠,散落在园中小径;
棚架上落尽叶片的寄生藤蔓
和一切娇美的鲜花,全都凋零不堪。
在风起和雪飘之间的时光,
一切令人憎恶的杂草开始生长,
粗糙的叶面上斑点密布,
象蟾蜍的脊背,象水蛇的腹部。
蓟草、蓖麻和毒麦之类,
酸模草,菲沃斯和阴湿处的毒芹,
都把中空的长梗伸出来
堵塞空气,闷死的风腥臭难闻。
还有名称不雅难以入诗的植物,
使这里充斥着畸形的低矮草木,
有刺的,多汁的,起疱的,青色的,
铅灰色的,沾着星星点点苍白的露水。
它们苔藓状的枝叶一片片腐败剥落,
粗壮的茎杆象处决凶手的火刑柱般立着,
零星的残皮剩肉仍在高处颤抖,
把疫疠传染给从旁经过的气流。
蘑菇,毒覃,各色各样的霉菌,
象迷雾从阴湿寒冷的泥土上升,
苍白而又肥厚,象腐烂的尸身,
感受了生命的灵气而又在活动。
菌丝,蔓草,垃圾,有毒的渣滓,
使流动的小河淤塞,不再喧响。
河口的菖蒲有如木桩,用它们的根子,
象纠缠成结的水蛇,形成挡水的坝墙。
在空气停滞的日子,每时每分
有毒的雾气不断升腾,
早上看得见,中午摸得着,到夜晚
形成星光难以溶化的浓重的黑暗。
油腻的陨落物飞掠、蠕动在花枝间,
在正午的天光下无法看见;
落在枝条上,这枝条
就被致病的毒液腐蚀而枯焦。
含羞草哭了,又好象有谁禁止啼哭,
用一对对闭合的叶片把泪水噙住,
泪水逐渐凝缩,
变成了冻结的胶状病毒。
叶片很快凋落,枝条
也很快被狂风的重斧砍掉;
叶汁从每一条孔隙收缩到根上,
象血液回流到就要停止跳动的心脏。
因为冬季快到了,风是他的鞭子,
向嘴唇伸出一根布满皱纹的手指;
从山岭间扯来一条条瀑布,
象锒铛做响的手铐挂在他的腰部。
他的呼吸是锁链,不声不响
就把土地、空气、流水全都绑上;
他坐着暴风牵引的车辇来了,
那风比北极的烈风千倍狂暴。
于是恶草,死亡的有生命的变象,
便逃到地下,躲避严寒的冰霜。
它们的枯萎和突然离去,
只不过象鬼魂的暂时消逝!
而在含羞草根部的底下,
鼹鼠和睡鼠却死于匮乏;
鸟儿从凝冻的空中缰死跌落,
接住它们的树枝已经***。
起先,下了一场能溶冰雪的雨,
那阴郁的雨水却又在树上冻住;
后来,寒冷的露水向上蒸发,
终于又变成温暖的雨点落下。
而北方来的旋风到处游荡,
象嗅出了死婴尸臭的恶狼,
摇撼这样阴郁、沉重、僵硬的树枝,
又用坚硬的爪子把它们攫去。
当冬季过去,春天又复归来,
含羞草成了没有叶片的残骸,
菌类、毒麦、酸模草和曼陀罗
却象死尸从毁坏的坟墓中复活。
茅茅
第3楼2009/01/24
结语
含羞草,或是在它的梗
腐烂以前,象个精灵
寄居其中的精神,现在是否
感觉到这种变化?我很难说。
那姑娘的,不再和散发爱情
(象星星散发光明)的外形
结合在一起的优美心灵,是否在
失去欢乐的地方找到了悲哀?
我不敢猜;但是既然在生活里,
一切都是表象,没有什么是真的,
充满了谬误、愚昧和纷争,
我们自己只是梦中的幻影,
那么,这虽是个简朴的信念,
考虑到它却足以令人开心颜,
那就是承认,和万象一样,
死亡的本身也必定是虚妄。
那可爱的花园,那美好的姑娘,
那里所有的美的气味、美的形象,
其实,从来没有消亡,变化了的
不是他们,是我们和我们的一切。
对于爱,对于美和喜悦,
不存在变化和毁灭,
它们的威力超越我们的感官,
感受不了光明是由于本身阴暗。
(江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