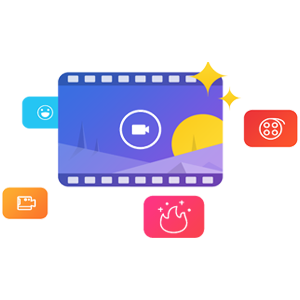2012年10月26日 来源: 中国科技网 作者: 塞尔日·阿罗什

今日视点
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法国物理学家塞尔日·阿罗什10月17日在《自然》杂志撰文,与读者分享了他获得诺奖的秘诀,并建议为年轻科学家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氛围。
自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获奖电话,经历接踵而来的媒体狂热追逐之后,我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深刻反思。但上周末巴黎阴雨绵绵,我也得以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深入探究过去几天来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诸多问题:我获得诺奖的成功因素究竟是什么?对年轻科研人员来说什么最为有用?当决策制定者准备倾听你的意见时,你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项目始于35年前,现在的同事、研究团队合作者杰恩·米歇尔·拉艾姆德那时是我的博士生。10年之后,随着米歇尔·布鲁恩的加入,我的研究团队成立。我们致力于原子和光子的研究,它们是量子世界的本质。当我们揭示某一预期的现象之后,曾经历过极度兴奋的时刻;同样地,我们也必须应对一些惨痛的失败实验,努力纠正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克服某些看似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难题。
在研究过程中,幸运这一因素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比幸运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成功主要依靠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独特的智力和物质环境。我在这里能够组建一支极其出色的永久性研究团队,我能够将长期积累的各种技能和知识不间断地传授给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研究生教授的课程,以及在过去10年间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课程,同样也为我获得诺贝尔奖做出了贡献,因为每年都需要准备一系列新的讲座,这使我能够专注于光与物质间相互作用的不同方面。
只有在稳定可靠的经费支持下,我们的实验工作才能取得成功,而这些经费主要是由管理我们实验室的相关机构所提供,欧洲和欧洲之外的一些国际机构也提供了必要的补充经费。此外,欧洲流动计划的灵活机制使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向来访的国外科学家开放,他们带来的各种新知识、技能和科学文化,使我们得以不断完善自己。在长期探索微观世界的过程中,我和同事始终都能够保持选择研究途径的自由,而不是以是否具有实用可能性和前景来衡量之。
不幸的是,无论是在法国或在欧洲其他国家,我所受益的环境对目前的年轻科学家来说几乎不大可能具备。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研究资源匮乏,再加上探索解决诸如健康、能源和环境等现实问题之科学途径的限制条件,人们更倾向于支持短期目标取向的研究计划,而不是长期的基础研究。科学家不得不提前阐明其所有的研究步骤,详尽列出每一个重要的研究阶段,解释清楚在研究方向上的所有变化。如果将科学研究的途径延展得太远,这不仅不利于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且也不能使应用研究达到其预期目标,因为许多实用设备都来自于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永远不会出自于事先设计好的蓝图。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观点过于悲观。目前,确实有一些机构(如法国国立研究局和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一些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项目,但对其资助的期限仅为3年至5年,这对于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来说实在太短。由于国家对实验室资助经费的周期性减少,因此年轻科学家进行的长期性研究经费不断缩减,毫无疑问,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类经费也不可能大幅增加。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年轻科学家欧洲研究委员基金,其资助期限应在10年以上,同时设立中期评估机制。
薪水太低是法国存在的另一问题。在法国研究机构工作的博士后,其初始薪水远低于那些由欧洲研究委员会基金支付费用的同行。随着资历的增加,其薪水将会随之增加,但年轻科学家(即便是非常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受困于薪水底层的时间过长。如果在这个系统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应该向这些处于薪水低洼地的年轻科学家倾斜。
我们可以不用花费任何代价就能获得不少改善。法国学术机构较为庞大,各种研究委员会、学校和政府机构相互交织,庞大的官僚体制困扰着科学家——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填写表格和完成报告,而不是从事具体的研究。因此,目前的这种体制呼唤简单化。
如果由于我的实验获得诺贝尔奖而能够吸引优秀的年轻学生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我将非常高兴。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类似于我和共同获奖者大卫·维因兰德曾幸运得到的经历——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研究目标,并且能长期地支配自己的努力,在看到光明之前有能力承担得起让自己驰骋在充满荆棘道路上的各项花费。
(郑焕斌)
《科技日报》(2012-10-26 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