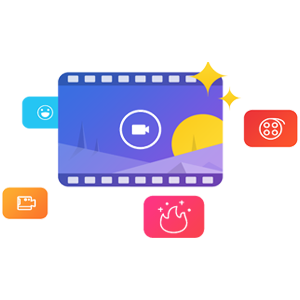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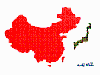
省部重点实验室
第1楼2012/01/04
神奇的开关
事情慢慢有了转机。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甲基分子(-CH3),它就像一个帽子:带上它,基因关闭;摘掉它,基因表达――被分别称为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甲基有些直接附着在DNA上面,有些则附着在某些和DNA纠结在一起的组蛋白上。当机体不希望某些基因信息被读取时,基因的“启动子”DNA就被戴上很多甲基帽,使得基因无法从那里读取,启动功能。
因此,即使携带遗传信息完全一样的两个个体,由于表达修饰上的差异,也可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状。
2001年,科学家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研究者采用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小鼠作为实验对象,来观察其皮毛的颜色。结果发现,小鼠们皮毛的颜色各种各样,从黄色到各种杂合色都有。让人意外的是,皮毛颜色的不同竟取决于它们从母鼠中继承的“agouti基因”甲基化程度高低。
2003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兰迪・朱特尔和罗伯特・沃特兰博士终于掀开了DNA甲基化的神秘面纱。
人们此前认为,在形成精子和胚胎前的植入阶段,细胞中的DNA甲基化几乎会完全重新洗牌,也就是说“基因修饰”没有遗传下去的可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某些甲基化是可以遗传的。
2007年,日本科学家在小鼠中发现,一种称为stella的蛋白质能够有效保护卵子中某些基因的甲基化修饰,并传给下一代。研究人员还得出结论,基因的甲基化或者去甲基化,和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虽然遗传信息没有改变,但环境的改变、丰富的经历、甚至不良的习惯,都有可能遗传给后代。
然而,这些对基因的表观修饰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它们又是靠怎样的机制遗传下去的呢?这一切曾经是个谜。不过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获得了一些信息。
2011年6月,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当果蝇处于胁迫条件下,它们会因适应环境而发生改变:原本紧密结合在“异染色质” DNA缠绕区的一种转录因子被释放出来,这些缠绕区域得以解开并进行复制。
表观遗传并非只是DNA甲基化这么简单。科学家们发现,对基因组的表观遗传修饰还包括组蛋白(可供DNA缠绕)的修饰、染色质的重塑、微小RNA的调节等诸多内容。
上帝的礼物
1939年,生物学家Waddington率先创造了“表观遗传学”这一术语;1942年,他认为生物体从基因到基因表型之间存在一种控制,这种控制机制就是“表观遗传学”。
算起来“表观遗传学”已经走过70多个年头了。不过,得以真正绽放异彩,其实也就仅仅10余年。
科普作家戴维・申克在作品《我们都是天才,是什么误导了我们》中写到,“人‘先天与后天之争’,因为表观遗传而显得苍白无力。表观遗传学可能是自发现基因后另一项最重要的发现。”甚至有人戏称,这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之所以称为礼物,是因为在肿瘤生成和治疗、干细胞分化等诸多领域,表观遗传学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研究人员发现,一部分DNA甲基化在肿瘤形成的早期发生了变化。并且,它不但对肿瘤早期转化起作用,甚至也能影响肿瘤的转移。
2004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首次批准了一种DNA甲基化抑制剂的新药――氮杂胞苷,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该药能通过去甲基化作用,提高“正面”基因的主导地位。据药品开发商Celgene公司介绍,重症病人服用氮杂胞苷后,寿命能延长约两年;而采用传统疗法的患者,存活期只有15个月。正因如此,不少技术人员对利用表观遗传学开发药物表现出极大兴趣。
例如,目前尚无好方法治疗药物成瘾。科学家发现,成瘾药物会导致脑区的基因调控水平的改变。即使戒药后,这些基因表达的变化仍可存月余,甚至导致病人终生心理成瘾。而表观遗传让饱受困扰的病人看到了曙光。正因为这份礼物非常厚重,所以关于它的研究持续升温,进行得如火如荼。
孙方霖认为,类似人类重大疾病、干细胞、体细胞重编程、衰老、神经科学研究等科学问题,其分子机制都离不开表观遗传调控。
而基因组学的科学家们,正尝试着找出某一特定群体之间表观遗传的差异,更好地诠释生命奥秘。
省部重点实验室
第2楼2012/01/04
拉马克主义归来?
19世纪初,法国人拉马克提出了“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的假说,该假说被称为“拉马克主义”。
比达尔文大84岁的拉马克,认为进化有可能在较短世代间发生:受环境选择,生物努力向优等方面进化,而达尔文却认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长久主题,进化存在于相当漫长的时间内。
一只长颈鹿可以很好地诠释他们之间的分歧: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祖先生活在缺乏青草的环境里,不得不经常努力地伸长脖子去吃树上的叶子,由于经常使用,颈和前肢逐渐变得越来越长,并且这些“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给后代;达尔文则认为,在某些个体偶然产生变异、脖子变长后,由于更适应自然,经过逐代积累,“长脖子”占据优势,完成缓慢进化。
在孟德尔经典遗传学――中心法则被确立为正统地位后,拉马克主义更是彻底被当时的人们所抛弃。
然而,表观遗传学的发现,却对经典遗传学构成极大挑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拉马克主义。这是因为,表观遗传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获得性遗传”。首先,可以从后天环境中“获得”性状;其次,这种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
那么,拉马克主义是否成功归来了?事实可远没有这么简单。毕竟,表观遗传还未被证明在任何外界压力下都会产生性状改变,不能够像DNA遗传那样,“一是一,二是二”,另外,一些缺失的环节仍然有待发现。例如有实验表明,表观遗传的印记在没有环境压力的数代之后,可能会渐渐丢失。
无论如何,获得性遗传现象的发现,足够令人深省。当人类获知生命奥妙的半径越大,基因调控这个大圆周长也就越长,圆面积也就越大。要知道,生命机制可远比人类预期要复杂得多。
科学,就是在构建――推翻――再构建中曲折前行。我们需要保持对自然的足够敬畏,或许哪怕一丁点儿的傲慢就将让我们与真理失之交臂。
即使拉马克主义不能归来,也到该为他正名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