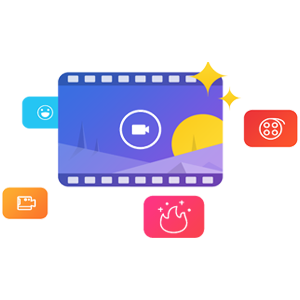


太白金星
第1楼2008/12/13
中国环保第一案
1979年9月12日,秋老虎肆虐江南。
江苏省苏州市市郊,人民化工厂储运组的工人张长林在下午4点差10分请了个假,因为妻子去上海参观,两个年幼的女儿无人照顾,他需要临时回家处理家务,当天晚上他必须加班。
离开前,张长林打开了一个阀门——浓度为30%的液体氰化钠将从150吨贮槽通向8吨计量槽。
张长林没有向同组的另外两个同事说明此事。从家返回单位后,张长林也忘记了那个盘子大小的阀门,以及缓缓流动的液体氰化钠。晚上8点多,他下班离厂。
第二天一早,储运组的同事最先发现了那个要命的阀门。他们看到液体氰化钠从贮槽的放空管喷到围墙上,再顺着防护堤的沟流向东面的一个洞,流到堤外的排水阴沟,而阴沟通向的,是贯穿整个苏州的京杭大运河。
当同事找到张长林时,张长林才想起了那个阀门,距离它的打开已经过去了15个小时。这名38岁的中年男人,有着23年工龄的先进工作者,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手中的饭盒“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9月13日,苏州市环境保护办公室和市防疫站在工厂排放口300米范围内测定,水中氰化钠含量高达47mg/L,超过地面水标准含量940倍。在人民桥、下津桥、渡僧桥、横塘大庆桥测定,一般都超标几十倍。七八十米宽的运河上,两岸的水草丛内,随处可见翻着白肚的鱼和张开壳的死蚌。后来经确认,从人民化工厂溢出的液体氰化钠共28吨,而人口服致死量仅为1-2mg/kg。
当天下午,苏州市环保办仅有的3名工作人员全部出动。从人民化工厂排放口上游1公里起,向南至30多公里外的车坊,他们坐船沿途一路宣传,发动村干部,号召民兵出动,告诉附近居民不能在河里洗菜,牛羊家畜不要饮用河水,不要用河水灌溉。
同时,他们发动上百艘船,让1000多名工人提着每袋50公斤重的硫代硫酸钠沿河撒入,以中和氰化钠,总共撒了10.8吨。
9月18日深夜,测定显示,运河水中的氰化钠含量基本恢复了原状。除了鱼、蚌,污染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事发6天后,张长林被苏州市公安局拘留,又过了3天,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由被逮捕。
当时,给张长林定罪名是个难题。10月27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参照当时已经颁布但尚未开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条,按照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张长林有期徒刑2年。
这是中国第一例对于环境污染案件的刑事制裁,被称为中国环保第一案。
或许是一个黑色的巧合。1979年9月13日,28吨液体氯化钠流向京杭大运河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获得原则性通过,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
太白金星
第2楼2008/12/13
环保的懵懂起步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
当时的中国,查遍所有字典,也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和束缚,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而事实上,环境污染问题在70年代初期已开始显现,大连湾、北京官厅水库相继发生大面积污染事件,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帮助中国将“环境”和“保护”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的,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曲格平。
70年代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率家人访华,周恩来总理问起了当时在国际上有反应的日本公害问题。他意识到,中国未来可能将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于是,举行了由中央高层和相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请日本访华团内对环境问题有深入了解的记者中野纪邦,就日本公害问题进行了全面介绍。迫于当时形势,座谈双方彼此不见面,记者在一间屋子里讲,其他人在另一间屋子里听。会后,又组织了讨论,主要议题是:如果中国出现类似日本的公害,该如何应对。
1972年,周恩来毅然派出了一个大型代表团,出席了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69年从化工部调入国务院的曲格平被任命为副团长。当时的考虑是,曲格平的专业是化工,算是对口。
曲格平说,那时的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理论上,大家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和中国的关系不大。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更多关注的是和美国的政治斗争,对美国在越战中一系列对环境的破坏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是在对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人家展开辩论的。比如什么是‘酸雨’,比如对于建立全球环境监测的提议,再如关于人口控制问题……”
在对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时,代表团成员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而世界谈论得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
太白金星
第3楼2008/12/13
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斯德哥尔摩大会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海洋、湖泊、森林、天空……很多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大问题。原来认为只是局部和部门的问题,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性的、必须从发展战略和总体全局上采取措施才能解决的问题。
回国后,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却并不知道还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曲格平是负责人之一。这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性机构,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环保机构。
环境保护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四次飞跃
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起草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提出“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围绕“先污染,后治理”,当时还有一场交锋。一派观点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在走同样的路,概莫能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超越西方国家。
曲格平则认为,西方国家因“先污染,后治理”付出了惨痛代价,在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此举将更加冒险。辩论十分激烈,经过不断地论证,经过反复的思想碰撞,最终许多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表示,不赞成“先污染,后治理”。
第二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在国务院所有部委里,环保部门是第一个有法的。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常设部门。
1982年机构改革,撤销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变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一个环境保护局。时年52岁的曲格平任第一任局长。
曲格平很快就发现,与各部门和地方的工作联系中断了。通过新组建的“城环部”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不仅程序繁复,而且受职权所限,几乎难以进行。
曲格平琢磨,如果在国务院设立一个不上编制的环境保护委员会,以组织和协调各个方面的环境保护工作,无疑是个办法。
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分管环保工作的李鹏副总理和分管机构改革的田纪云副总理的重视。当时国务院正在大力清理撤销非常设机构,但还是作为一个特例,决定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由李鹏副总理任主任,30多个部委领导人做委员,办公室就设在国家环保局。
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上,刚成立的环保局再次收获“大礼”。和计划生育一样,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为了跟基本国策配套,当时还制定了“同步发展”的方针。按照方针要求,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现在仍在沿用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政策都在这一年确定下来。
1988年,国务院再次机构改革,国家环境保护局脱离建设部,成为直属国务院管理的副部级单位。
9年后,国务院面临又一次机构改革,在听到国家环保局的规格没变化时,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找到已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的曲格平,希望能向朱镕基总理再争取一下,把国家环保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
太白金星
第4楼2008/12/13
第二天,曲格平向朱镕基总理汇报了环保局改为环保部的必要性,但朱总理说,国务院机构调整方案中央已经定了,现在再增加一个部已经不可能了。“我说,能不能改为国家环保总局?总理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以后在公布的机构中,环保局果然变为总局了。”
1998年,在国务院撤销了多个部委的情况下,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
十年之后,“大部制”背景下的部委整编中,环保总局再次“逆流”而上,成为环保部。
曲格平说:“环保机构的不断变化与升格,反映了政府以及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断加深。”
环保困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曲格平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期间。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尽管当时政府已经初步形成了环保法规体系,但它们根本抵挡不住过热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在曲格平看来,所有人的精力、注意力都在搞经济发展追求GDP的增长,而对于环境保护,虽然提还是提了,但是实际上摆不上议程。
“当时他们认为排放污染物天经地义。国家要我的产品,没有说要我其它的东西,治理污染可以,你来治理。”曲格平很无奈,他担心这样下去,中国终会陷入环境困局。
曲格平的担心在沙颍河得到了印证。22岁的何玉明从小生活在沙颍河边的河南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
在他的记忆里,村口的沙颍河流的一直是黑水,如果哪天看不见黑水了,那一定是河面上有一层厚厚的泡沫,泡沫可能是很多种颜色,比如白色、黄色或者红色。很长一段时间里,何玉明都认为水就是黑色的,并且会带着刺鼻的腥臭味。因为他每天喝的水也是这样的颜色和味道,尽管饮用水是从家中水井或水塘里打取的。
让沙颍河河水变黑的是沿岸遍布的化工厂和造纸厂,而沙颍河最终注入淮河。
“黑水”给何玉明带来了噩梦般的童年,他的爷爷奶奶以及三个远房叔叔,都在90年代陆续死于癌症。在何玉明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为胃癌去世。
在何玉明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拉稀生癌。
何玉明最怕听到有人说身上不舒服,村里人只要感觉有病,一检查就有可能是癌症。沙颍河两侧的村子,村民经常会身体不舒服。
除了癌症之外,各种疑难杂症也频繁出现在村民当中,畸形婴儿比例也大大提高。何玉明同样没有幸免,20岁的他患有严重的胃炎和肠炎。
2004年,18岁的何玉明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次走出家乡。他在图书馆上网了解到,早在1994年,国家便开始了淮河治污行动,十年来累计投入数千亿元,却污染依旧,甚至更多的废水废渣被排入淮河。
何玉明说,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感觉心里堵得慌”。想到了病逝的亲人,和散着异味的黑水,何玉明睁着眼睛哭了一夜。
全民环保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有关部门曾经希望在十三陵附近建一座水泥厂。知道这个消息后,环保局多次要求主管单位不要建厂,但对方却执意要开工,一争就是好几年。最终,官司打到国务院,这个水泥厂才被勒令停止建设。
曲格平的继任者解振华也曾说过一个故事:基层环保执法人员到一家发电厂检查,这家发电厂的负责人当场甩出120万元说,法律规定,环保部门例行检查一个月只能一次,每次罚款不得超过10万元。我给你120万元,就把一年内有可能被罚的钱一并交清了,环保局以后也不用来了。
就像早年间美国在环境立法方面面临的问题一样,中国关于环境方面的法规,虽然覆盖面很广,但执行力很弱。
1993年,曲格平调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在任十年,曲格平参与主持了多部环保法案的立法工作,他参与制定的最后一部法律《环境影响评价法》最让他刻骨铭心。为了这部几乎流产的法律,老人曾疾呼:“《环评法》不通过,我死不瞑目。”
《环评法》的制定经历了少见的激烈争论和强烈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们大都赞成和支持这个法律草案,只是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反对意见主要来自国务院有关部门,除两个部门表示支持外,草案所涉及到的主要部门大都持反对意见。
由于相关各部门难以取得共识,以致这部法律的草案被迫中断审议20多个月。按全国人大立法规定,一个法律审议中断两年便自动撤销,并不再重审。
曲格平将《环评法》称为全国人大唯一一部起死回生的法律。就是这部法律,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持续的风暴。
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大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等多家大公司的30个项目叫停。理由是这些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
不久,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公开表示,“环境影响评价决不是橡皮图章”。之后几年,潘岳也用一年一度的“环评风暴”兑现着承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检查报告,《环评法》实施5年,近1.5万亿元的377个“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项目因环评“下马”。
在赋予权力的同时,环保部门也承担着同样多的责任。2005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在不断付出环境代价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地方政府开始在GDP和环保的博弈中倾向后者。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在沿海地区大量关停,环保项目则越来越受欢迎。
在实行了“限塑令”之后,带环保袋上街购物,成了越来越多民众的选择。抵制一次性筷子、不使用纸质贺卡更是蔚然成风。
正如NGO组织“自然之友”的一句口号:真心实意,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