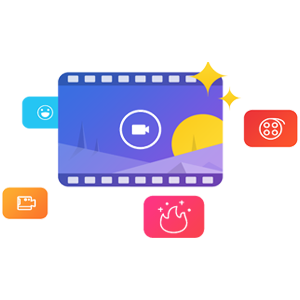

醋老西
第1楼2007/07/22
黄祖洽:我现在还是个学生
——记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
黄祖洽,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生于湖南长沙。先后从事原子分子理论、原子核理论、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以及输运理论的基础研究。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对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作了理论计算并纠正了苏联专家设计的临界大小数据的错误。近年来开展了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浸润相变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作为主要作者之一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第一作者的《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黄祖洽不大的办公室里,满满的书柜,简单的桌椅,戴着黑框眼镜、穿一件素净衬衫的老人,一切都平淡素雅,让人无法与曾经发生过的惊天伟业联系起来。他,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氢弹理论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有着辉煌的历史,却给人从容淡泊的感觉。
“核武”专家当上了大学教授
1980年,黄祖洽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此前,他一直从事原子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1958年领导并参与了核潜艇用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1960年开始领导“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理论进行预研,次年开始参与原子弹设计中所需状态方程、中子运输、中子爆炸装置等的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1965年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参与氢弹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黄祖洽为什么选择了教书育人作为最终的事业?“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先生这样告诉记者。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他在1970年到干校劳动学习时对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反思。
黄先生回忆,在九院理论部的研究工作是分工明细的。按照专业,理论部下设研究室,室下设研究组,每个组里都有一些大学生。每个部门都担任着不同的工作,他当时任理论部副主任,同主任邓稼先、副主任于敏等人担负着最基础、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各室主任就负责编写大型的计算程序,用数值方法解方程;而大学生的工作主要是昼夜轮流地在计算机上演算求解。
之所以要这样明确分工,黄先生解释说:“当时的核武器理论研究不可能借鉴国外,所以他们这些经过理论物理研究训练的人就承担了基础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分析物理现象,推导方程,提出方案。光有方程不行,还要解方程,这些非常复杂的方程都要靠数值方法来解,这样就要先编出计算程序,然后再计算。那时的计算机还比较落后,计算程序编出来以后还要用纸带穿孔昼夜计算,所以那些大学生就轮流值班上机。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黄祖洽意识到这种分工明确的做法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而言是极其有限的。“不让他们从头做起,在理论上、基础问题上,他们就不完全了解,这样对培养年轻人不利。”文革时期,学校秩序被打乱了,黄先生觉得“中国人才的断层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后来他回到研究所,一方面做研究,一方面开始考虑怎样培养年轻人。1980年,“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已获突破,又赶上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来承担教学工作,黄先生有意到大学里做培养年轻人的工作,于是,核武器专家就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醋老西
第2楼2007/07/22
人生的第二次辉煌
有人曾说黄祖洽是“一生两辉煌”,一是中国核反应堆工程和核武器设计的奠基者,二是手执教鞭,为我国理论物理事业培养继承人。
黄先生自己也乐此不疲,今年已是八十高龄的他还担任着120多人15讲的本科生课程。他说:“当老师的成就感倒没有多想,但是我觉得心情很舒畅。至少没有白吃人民给的饭,到时间就去上课。”到现在为止,黄先生已经培养了10多位博士生,北师大物理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也因他的不懈努力大有提高。他的“述怀”诗中“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表达了他对青年才俊出现的满腔喜悦。
谈到在北师大教书育人20余载最大的感受,黄先生觉得我们的国家人才辈出。成才靠自己,但也需要适当的条件和指导,作为导师,最关键的就是怎样启发和鼓励,帮助他解决困难。
黄先生就是一位善于启发引导、敬业奉职的导师。他指导研究生读文献,自己先要仔细研读一番,即便现在视力下降还要拿着放大镜读文献上很小的字,所以他和学生们做着一样的“作业”;每个星期,他要和自己的研究生讨论一次,让他们介绍工作进展,相互提问题研讨;学生写的文章他都一一看过,从理论论述到数学推导,甚至文字笔法,他都要给他们改。
正是这样的孜孜不倦、一丝不苟,20余载黄先生的门下只有10多位博士生,硕士生更是屈指可数。他告诉记者:“一个博士生要念三年,我大概每届招一个学生,如果要同时指导超过三个学生,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就不够了,要暂时缓一下。”他说很佩服那些同时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的导师,但是他自己肯定做不到:“培养一个博士生要花很多脑筋和力气。我还是倾向于师徒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现在黄先生还带着一位博士生,他说这是封门弟子了,今后要给精力充沛的年轻教师更多机会。“给本科生讲讲课更适合我现在的状况。”黄先生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说。1999年,他开始给物理系和低能核物理研究所的大一新生上《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能容纳140多人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当当,除了120多人的选课学生,还有外校来的进修教师和旁听生。全部15讲都是黄先生亲自上阵,从来不点名。
吸引学生的是黄先生精彩的演讲和有趣的故事。他告诉记者,物理学前沿范围很大,真正要讲起来需要高等数学的基础,但是大一的学生还没有学过,他就着重介绍物理学前沿内容,讲物理学家的故事,其中也蕴含着很多做学问的道理和态度。
给本科生上课似乎比指导研究生更让黄先生感到满足。他的多名研究生都去了国外,黄先生有诗曰“雏燕离巢去,良材异国移”,无疑是他痛惜人才流失的写照。给本科生上课有100多人,他说:“即便将来出去几十个人,还是会留下几十个人。”现在上本科生的课或许是他最大的慰藉了。
在课堂上获得很多乐趣的黄先生认为,教授,教授,教书是本职。他说:“当教授去讲课是理所当然的,当教授不讲课就是不正常的。”这或许就是他觉得时下要求教授给本科生讲课是一种怪现象的原因吧。
以学生自居的大学教师
“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学生的心态。”一句话让记者大吃一惊。“因为我还是不断在学。”黄先生坦然说。
教研究生或者本科生,都会遇到学生提出的问题,这就促使他想得更多,有时候还要去查资料,找书看,再学习,所以黄先生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他告诉记者,现在的生活日程和学生也差不多,每天都到办公室来,已经成了生活习惯。看到喜欢的书还是和以前一样捧着读起来。他从小就爱提问,现在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周的讨论他也喜欢向学生提问,他觉得这就是学生心态的表现。
《三杂集》是黄先生即将出版的一部书,所谓“三杂”即“八十杂忆”,“杂文”和“杂诗、词、联”。他在“八十杂忆”这部分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开家,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地长大。”印证了他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学生的心态。
“八十杂忆”记叙了黄先生从小学到大学教授的一生,虽不完整,但拾取的是记忆里最璀璨的“珍珠”。“少年作文十篇”都是作文课时写的文言文,当时他16岁,是他的母亲留下了这个珍贵的作文本。其中《读庾信小国赋书后》一文,老师的批语是:“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勉之望之。”“季绳”是黄先生的字,老师的意思是动员他研习文学。
年纪轻轻饱读诗书,文笔初露锋芒的黄祖洽却没有走上文学家的路,他对数学和物理学很感兴趣,“许多现象,许多问题,你能通过物理学了解它的原因”,他说。上高中时,他所在的学校没有物理老师,他就自学,到图书馆借书,从老师那里借书,还没上大学,他已经把大学数学和物理学得差不多了。
对少年黄祖洽而言,读书有无穷的乐趣,《史记》、《庄子》之类古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等,他都饶有趣味地读。所以在他的“八十杂忆”里才会有一篇短文叫《读书玩》。
“兴趣”支撑着黄先生从动荡的少年求学时代一步步走过来,投身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最终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好学不倦,以学生自居,从他身上能体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李晨)
来源: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