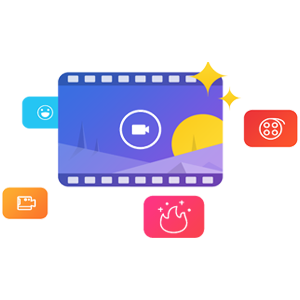

智慧的弟弟
第1楼2007/08/12
姚兰是个朴素极了的姑娘,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映衬着未见成熟的圆脸蛋,在那稚嫩的脸蛋上有一双黑黑细长的眼睛,那眼睛只要在不生气的时候就向上弯成一个弧度,总给人笑眯眯的感觉。虽然她脸蛋幼稚,但她身体却发育丰满、曲线分明,个子不低,就是有点胖。她身上一条碎花圆点拖到脚踝的连衣裙几乎把她奶油色的皮肤全部包裹起来。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密密麻麻的上自习课的学生中间她的长相和打扮无疑是那种不引人注目的女孩。
教室里很闷热,夏日的夜晚几乎没有一丝凉风。姚兰回到教室后头很疼,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三哥的影子不断浮现在她面前,那让她既爱又恨的影子。那些与三哥在一起的日子又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那因为她而被打得青紫的脸孔,以及后来骄傲得意的笑容都是那么让她心酸不已。在她幼年的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三哥为她和四个小子大打出手,最后被打得破衣烂衫、满脸是血的回家。而那次三哥回家后却又被老爸暴打了一顿。
三哥是家里惟一一个叛逆少年,姚兰的两个哥哥以及姚兰自己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从来不给父母惹麻烦,惟有三哥和他们不同,从小就特叛逆。三哥是她哥哥们中惟一被父亲暴打过的孩子。父亲对他们的严格教育和独断式培养造就了她和她的大哥、二哥的体制化性格。在四个孩子中惟有三哥是敢于和父亲顶撞的,对父亲犯尊妄上,在上中学时三哥结交了一帮社会混混儿,最终导致后来犯事进监的结果。
三哥这次进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是第三次,前两次姚兰的父母都托关系把他弄了出来,没想到没过多久又被抓了进去。这次姚兰父母打定主意不再管他,要让他好好吃吃苦,接受一下教训。
她回到教室后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满脑子都是三哥的事。她翻来覆去想解救三哥的办法,但对她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天大的无法完成的任务。
去找爸爸!她最后打定了主意,尽管三哥和家人那么对立,但这个时候家人是不会不管他的,她了解爸爸。于是,她飞快地收拾了书包,离开教室回家去了。
智慧的弟弟
第2楼2007/08/12
父亲在客厅里看书。姚兰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像贼一样轻轻推开门,向里面张望了一下,然后溜进书房。
“你又想偷什么?”父亲头没回就问。
“你又发现啦!”姚兰丧气地说。
“就你那点小把戏,你爸早领教过无数次了。”
“那你不会装装样子别把我戳穿!”
父亲转过头,笑了起来,“好!下次一定让你得逞。”
女儿一屁股坐在父亲腿上,揽住父亲的脖子,在父亲的左右脸蛋上各亲了一口。
“又有什么事要求我啊。说,什么事?”
“不能说!”
“什么事不能跟你爸爸说啊?”
“是关于——怎么说呢!不好说。”
“你找男朋友啦?”
“说什么呢——”
“那是什么?”
“我说了你别生气。”
“什么?好,爸爸我不生气。”
“好!你说的。是我三哥的事儿。”
“那小子——他怎么了?”
“有人要害他。”
“害他?我看他害别人还差不多。”
“真的!”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害他?”
“三哥今天托人带了个口信给我。”
“带了口信?怎么回事?”
姚兰把当晚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只把披头三兄弟在楼下乱喊的情节略了过去,重点讲了谈话的过程。
父亲沉思了片刻,感觉很有必要认真对待。尽管他此时挺恨自己最小的儿子不成器,但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舐犊之爱让他必须面对自己孩子可能遭遇的严重事态。
“叫他来!我想见见那个叫披头的。”父亲站起来恨恨地说,随即从桌上烟盒里抽出枝烟点燃。
智慧的弟弟
第3楼2007/08/12
姚兰找披头费了很大的劲,她拐弯抹角多方打听才知道披头真名叫王谦,是大学城外东方钢厂的职工子弟。钢厂破产以后,整个厂区就一直闲置,年轻有本事的职工都各奔活路去了,只有一些年老力衰的老人还留在厂区里,另外还有一些家教不严或者就像披头这种父母离异的孩子像自由的鸟一样在无人看管的破败世界里游荡。
姚兰穿过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拐进一个篮球场,在破旧的球场边,她看到几个十八九
岁的野小子在抢一个破篮球。她想过去问问路,但看那些小子玩兴正酣,似乎不好打搅,于是她踌躇顾虑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一个声音从远处一侧的墙角传来,一个男孩身子斜靠在墙上吊着眼睛看着她喊:“找谁?”
姚兰顺着喊声望过去,她被男孩火辣辣的目光所惊愕。她鼓起勇气应答了一声:“我找王谦!”
“王谦?哪个王谦?这里没有叫王谦的。王爷你要不要?”男孩不怀好意地说。
“王谦,就是——就是那个叫披头的大哥。”姚兰急急地说。
“找披头就找披头,什么王谦,我还不知道披头叫王谦。”角落里的男孩态度收敛了一些,“你找他什么事儿?”
“我爸找他有事儿!”
“你爸?你爸是谁啊?”
“我爸是省军区的。”
“哦——!”男孩惊讶地后仰了一下身子,脸上露出疑惑、不安的神情。半天他才问了句:“你说的是真话?”
“是啊!我不骗人的。”
“那你爸找披头干吗?他犯什么事了?”
“他没犯事,是我三哥的事。我父亲想找他。”
“那你等等,我去叫他。”男孩说完一溜烟跑了。
智慧的弟弟
第4楼2007/08/12
一会儿,男孩跑了回来。
“披头让你去!跟我来!”男孩向姚兰招招手。
姚兰跟在男孩屁股后面高高低低左拐右拐走了一阵,才在一处大厂房的门口站住。男孩推开一扇小门钻进去,姚兰也随后跟了进去。瞬间,她感觉到一丝丝凉爽,眼前黑蒙蒙一片
,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她站立了片刻,才感觉有些适应了。
“在这边!”男孩在远处一角朝她喊,“过来!”
姚兰小心翼翼地穿过厂房里巨大的机器和散落在地上生锈的金属物件,她生怕滑倒。姚兰环顾四周,斑驳的墙壁和发黑发暗的顶棚以及拉得到处都是的电线散发着神秘幽暗的气氛。
姚兰胆战心惊地走到男孩招呼她的角落,在角落边,有一扇小门。男孩把门推开。
“披头在里面等你。”男孩恭敬地说。
姚兰走进门去,发现里面乌烟瘴气,一股刺鼻的烟草味儿让她窒息。她被呛了几口,连连咳嗽,她使劲拍拍胸脯才算平静下来。绕过一堆纸箱,她看到在房间最里面亮着一盏昏黄的吊灯,灯吊得很低,有四个人围在灯下在玩麻将。在墙角有一张床,床上七扭八歪地堆着可以称为被子的东西,在床头边有一个小桌,上面放了台电视。离小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书架,上面堆积了一堆老旧杂志,在书架旁边则摆了一堆空啤酒瓶子。
姚兰远远地站住,看着打牌的人不吱声。她看见披头面对着她,但却根本不抬头看她,就像她不存在一样。
就这样过了好一阵,不知谁和了牌,打牌人都把手中的牌推倒了,这样,披头才把头抬起来。
“找我干吗?”披头靠在椅背上看着姚兰懒洋洋地问。
“我——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没看我在忙吗?”
姚兰不吱声,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哎!求你个事儿。”披头冷冷地对姚兰说。
“什么?”
“你带钱没有?”
“干吗?”姚兰警惕地问。
“我今天手头不顺,想问你借点钱。”
“你要多少?”
“你手头有多少?”
“我就这点儿!”姚兰怯生生地从背包里掏出钱包,把钱掏出来摊开给披头看。
“你也真是穷鬼!全给我吧。”披头朝姚兰招招手,让她把钱送过来。
姚兰慢腾腾地走过去,把钱递给披头。她嘴唇嚅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放心吧!我等会儿赚回来还你。不就两百块钱嘛,我看还没两百,最多一百八。好了,等会儿还你两百。”
“钱我不要了,你给我留两块钱车费就行了。”
披头眼睛瞪了起来,惹得周围三个牌友笑了。
“我说你是真不明白事还是怎么的?你以为我蒙你钱是不是?”披头恶声恶语地说,“我披头说还钱给你就还钱给你。你,先一边坐一会儿,等我打完这圈再和你谈事儿。”
姚兰在角落里找了个纸箱坐下来,默默地等待披头完事。在这时,姚兰才仔仔细细打量起披头来。
这是个长相挺英武的小伙子,浓厚的眉毛,挺直的鼻梁,线条分明的嘴唇,黑色长发悬垂在脸颊旁,嘴上叼了根香烟,眼睛因为烟雾的刺激时常眯缝着,从姚兰这个角度看过去,能看到披头的脸部的半个侧影,但那侧影由于叼烟造成的嘴唇歪斜而使左半个脸部也歪斜着。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没洗脸的缘故在灯光下他的皮肤蜡黄,身上的一件宽大的白色圆领汗衫看上去黑糊糊满是斑斑汗迹。姚兰一边看披头一边心里寻思对面的这个混混儿,他到底靠什么生活?对他每天就这样打发时间她感觉不可理喻。在她心中那些美好、光明灿烂的事物似乎与这群人丝毫不沾边。看披头也就二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比她也大不了多少,但生活似乎给予披头这种人的东西更让姚兰感觉到震撼和惊讶。酗酒、抽烟、赌博、打架,甚至偷窃、抢劫,也许还有强奸,她简直都不敢想下去。此时,她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感。披头不会打我的主意吧,她恐惧地想。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闯到这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智慧的弟弟
第5楼2007/08/12
姚兰足足等了一个钟头才等到披头完事,看披头的脸色就知道他输了个干净。
“不玩了!”披头把牌推倒在桌子上,然后揪住一个牌友说:“你今天赚了,借我两百!”
“不借!你小子没钱还。”牌友把他抓衣服的手扭开。
“真不借?”
“牌桌规矩你不懂啊,你这样以后我们怎么玩?”
“那好!你们走吧。”披头丧气地朝三个牌友摆摆手,颓然靠在椅背上。
牌友走后,房间里只剩披头和姚兰两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姚兰感觉披头的样子很是可怕。那像死人一样的肤色,没有良好睡眠而倦意稀松的眼睛,长长地垂落在脸颊上遮住半个脸的黑发,以及像鸡爪一样瘦骨嶙峋的长长的手指都让人联想到病态、发狂的疯子。
姚兰默默地看着披头,她等披头说话。披头垂头丧气两手放在桌子上发愣,他呆呆地坐着,直直过了五六分钟才打破了沉默。
“抱歉!”披头声音此时异常柔弱,“我把你的钱也输了。”披头眼睛盯着墙角,不敢看姚兰。“不过我会还你的。要不这——”披头指了指电视,“你等会儿把这个搬走。”
“没关系!你不用还我。”姚兰低声说。
“要还的,我说话算数。”披头语气坚定地说。
姚兰没再吱声。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披头昂起下颌,恢复了以往的傲慢。
“我父亲找你,想了解我三哥的事!”姚兰低下头嗓音低低地说。
披头听完两眼直直地看着姚兰,足足有十几秒钟,然后说:“我说你小丫头是不是有病?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跟你父母说吗?你怎么没一点儿信用。”
姚兰不去反驳,她知道自己违背了承诺,另一方面她根本就不想和对面这个气势汹汹的男孩争辩,她觉得和这样的男孩解释那是白浪费时间。
披头见姚兰不说话,另外他的火也发得差不多了,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于是问:“你老爸找我什么事儿?”
“他想了解我三哥的情况。”
“那你老爸是想帮你三哥了?”
姚兰点点头。
“哦——”披头偏头想了想,“你老爸要是出马,那你三哥应该没什么事了。看来你老爸还是不错,你三哥有你这样的老爸真是他的福气,看来人和人不能比。好吧!是现在去,还是约个时间。”
“你明天下午有时间吗?”姚兰问。
“我——”披头看看顶棚,笑了起来,“我天天有时间,我时间一大把。”
“那你明天下午三点到我家来吧。”
“你家我没去过,听你哥说你家住军区大院。好像我这种人进不去。”披头自嘲地说。
“没关系,我到时候在大门口等你,我带你进去。”
“那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那我走了啊!”姚兰站起身对披头道别。
“等等,我送你出去。”披头站起来。
“不用!”
“不用什么?钢厂到处都是像我这样的,像你这种学生妹不被抢才怪。”
“不会,我来的时候就没出事。”
“那是你运气!告诉你,刚才给我递口信的那小子就准备对你动手,幸亏你报了我的大名。”
“哦——”
披头陪姚兰出了厂房,然后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过篮球场的时候,披头让姚兰等等,他走到球场边,拽住一个小子,从那男孩裤子口袋里搜出了几个硬币。
“给你,坐车够不够?”披头把手头的三个一块的硬币递给姚兰。
“够了。”姚兰说着接过硬币。
披头把姚兰一直送到大门口,指着车站说:“那是车站。好了!你现在安全了。”然后用叮嘱的口气说,“记住,以后别到这儿来,这里乱得很。”
“知道了。”姚兰点点头。
智慧的弟弟
第6楼2007/08/12
第二天整个上午,披头都在床上睡觉。每到早晨的时候,他脑子总是处于一种半醒半睡之中。脑海里时常出现他幼小时的生活场景,以及和父母在一起的欢乐的日子。他至今不明白感情甚笃的父母为何要离婚,为何他会成为一个弃儿而得不到亲人的呵护。如果不是离婚也许爸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也许自己不会像现在这样放纵和毫无希望,他想。
在很多时候,披头一个人坐在床上默默流泪,为自己苦命的父亲,为毫无音讯的母亲,
以及自己的厄运而痛苦难过。“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他妈的运气,我没有别人的好运气,没有一个好家庭,没有好父母来给我一丝希望。”他恨恨地想。他恨那些日子过得好的人,恨每天衣着光鲜,傲慢得意的社会宠儿。自从他十岁离开母亲,十二岁失去父亲开始,他的生活就与厄运相伴,他从此失去了童年幸福和少年欢乐,逃学、打架成了他生活中每天经历的事情,他的爷爷奶奶丝毫不能阻止他向往自由的天空和野性的召唤。就这样,他在流血和拼杀中成长起来,在阴暗、晦涩的角落里积聚着仇恨和愤怒,在街头的欢闹中增长着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在多次的暴力行为中强壮着体格和胆识,除了他的目光越来越阴郁冷酷,越来越锐利之外,他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恶感却不见半点好转。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披头越来越对生活和生命感到迷茫。他的头发越留越长,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人的目光,他有一双艺术家修长秀丽的双手,但这双手却时常握着菜刀、铁棒四处拼杀,他手臂和后背伤痕累累,头上也被人用砖头砸开花过多次。他虽然没有健壮的体格,看起来挺瘦,但却满身是肌肉,他打架既狠又准,逐渐在钢厂这块地头叫响了名气。
披头有两个兄弟,一个叫陈海忠,外号黑皮,另一个叫范红军,外号冬瓜,他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共同的成长经历让他们有了相同的心理,这种从小就培养的感情使他们在长大后都具有了强烈的凝聚力。他们三个结成了钢厂的一个小帮派。
中午的时候,披头从床上爬起来,拿了毛巾走到厂房里一个角落的水龙头边,拧开水龙头把毛巾打湿,他用水冲了冲头,然后他洗了脸,再用拧干的毛巾把脸擦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坐在水龙头边的一块钢锭上,猛猛地吸了几口,感觉自己舒服了一些。他想了想今天该到哪里去吃饭。钢厂外的小食街上有六七家是他收保护费的,每天他也在这几家轮流转着吃白饭。
他回到自己的黑房子里,从床头拽了条裤子穿上,然后套了件T恤衫。他用梳子把自己长长的被水打湿的头发梳理顺了之后,就向厂区外的小吃街走去。
在小吃街他进了一家面馆,老板见了他非常恭敬。这家面馆是受披头保护的,老板每月要给他三百元保护费。另外,他也会时不时来这里吃上几顿。在披头的保护下,左邻右舍就不会有与面馆相似的馆子再开,另外也没有街上的地痞流氓来找老板的麻烦,从效益这方面讲,老板还是挺划算的。有时候,披头也去为老板收账,有些单位的食客拖欠饭款事情也基本能被披头摆平。披头要的账一般与老板二八分成,披头拿二,老板拿八。这样,披头算是有那么一点收入能维持自己的日常开支。
披头要了碗面,扒拉了几口很快吃完,然后要了碗面汤,吃饱喝足。他把老板叫了过来。
“我想把这个月的钱提前收了,我有件急事需要办,不知能不能行?”披头态度和蔼用商量的口气说。
“没问题!”老板拍拍他的肩膀,“你我还讲什么客气。你现在就要?”
“是!现在就要。”
“那你等等。”老板走到收款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三张百元钞票,随即递给披头,“这是这个月的。你要是不够用我再给你拿些!”
“不用!够了。”披头点点头,面色平静地说。他把钱随手装在T恤衫的口袋里,然后就出了门。
披头找了家录像厅,看了两个小时录像,看时间差不多了,他出门在街口打了辆的士。
“去军区家属院。”他对的士司机说。
智慧的弟弟
第7楼2007/08/12
姚兰早早就在门口等披头来。她在大院门口一家冷饮店里吃了足足三大杯冰激凌才看到披头从的士上下来,于是她急急付了账跑出了店门。
“我在这儿!”她朝在大院门口东张西望的披头喊。
披头看到姚兰穿过马路朝他跑过来,于是左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右手向姚兰打了个响指
,随即用食指点了一下姚兰,算是给姚兰打了招呼。
“我老爸去军区开会,要四点才能到。”姚兰气喘吁吁地说。
“那怎么办?我不能在这大太阳下等你老爸一小时。”
“不用。你在我家等他,家里有空调,一点也不热。”
“哦!那好,如果能再给我烟抽就更好了。”
“我老爸有,我等会儿给你偷来。”姚兰说着就带披头走向大院的大门,她向门前的警卫打了个招呼披头就被允许通过了。
智慧的弟弟
第8楼2007/08/12
披头头一回进这个警卫森严的大院。姚兰领着他沿着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穿过一片松树林,来到一栋四层楼前,楼从外表看已经有些年代了。楼的外墙壁上爬满青藤,在阳光的照射下青藤叶子闪烁着绿油油的光彩。披头走进去发现楼里的过道很朴素、干净,凉意阵阵。
姚兰带披头上了三楼,姚兰掏出钥匙打开一扇门,披头从姚兰的肩头望过去,看见房间里的陈设朴素,丝毫不奢华。走进房间,披头感觉房间很大,尤其是客厅,足足有五六十平
米。
“你这是几室的房子?”披头问。
“是四房一厅的。”姚兰请披头坐下,一边跑到冰箱旁边,打开冰箱给披头拿饮料。
披头并没有坐,而是在房间里四处张望。
“你家够阔气的哦。”披头感叹道。
“我家不算什么,大院里很多家比我家阔气。”姚兰在杯子里加了冰块,然后把果汁倒进杯子里,把杯子放在茶几上。
“你老爸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这我不能告诉你!”姚兰笑着说。
“是军事秘密?”披头问。
“不是!我父亲不让我们乱说。”
“不说拉倒!我没心思打听你家的破事儿。”披头转悠了一圈后回到客厅,坐到沙发上。“我想抽烟!”他对姚兰说。
“你等等哦。我去看看我老爸的烟还在不在。”姚兰做了个怪相,然后推开书房的门钻进去,披头听见书房里姚兰翻腾东西的声音,过了一阵,姚兰拿了包香烟出来。
“你看这烟行不行?”
“什么烟?我看看!”披头从姚兰手里接过香烟,立刻就两眼放光。“我说你丫行啊!你把你老爸的中华烟都拿来啦。”
“这烟好吗?”
“好!当然好了,五六十元一包。”披头把烟打开,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一副陶醉的神情。
“啊!这么贵啊!”姚兰惊讶道。
“得!算哥们儿没白来。”披头立刻抽出一枝,掏出打火机点燃,然后把二郎腿翘起来,神情悠然自得,似乎像是在自己家一样。
“你要是喜欢就把整盒都拿走算了。”姚兰见披头那么钟爱地把玩手中的香烟于是说。
“你说真话?”
“当然!”
“你不怕你老爸生气?”
“我不让我老爸知道。”
“哦!既然如此,我就收了。”披头把烟装进裤子口袋,然后他突然想起上次借钱的事。
“对了!上次借你的钱我带来了。”说着披头从T恤衫口袋里掏出钞票,点出两张放在茶几上。
姚兰脸红了,她说:“我说了不要了,你拿回去吧。”
“玩去——”披头轻蔑地回了一句,“我可从来不占女人的便宜。”
“那我还你二十。”
“不用!我说了还你两百。”
“那我也要还你。”姚兰说着跑回自己的房间,一会儿拿出二十元,递给披头。
“哎——我说你这丫头挺较真儿。也好,我正缺钱用,不拿白不拿。”说着把二十元钱收进口袋。
披头在舒展地抽烟喝饮料的当口,发现了角落里的钢琴。
“那边那个黑家伙是钢琴吧!”披头指着放在角落里的钢琴问。
“是!”
“谁弹?”
“我!”
“你——”披头笑起来,“你会?别逗了。”
“骗你干吗?”
“不信!”
“那我弹给你听!”姚兰说完走到钢琴边,掀起琴盖。“你想听什么?”
“我哪知道你会弹什么。随便弹,爱弹什么弹什么,最好来个猛的。”
“猛的不会弹,给你弹《少女的祈祷》吧!”
“好,爱怎么祈祷怎么祈祷,好听就行。”
智慧的弟弟
第9楼2007/08/12
姚兰屏住呼吸,然后沉静了一下心情,手指轻轻按了下去,立刻,如幽谷溪流般动听美妙的琴声从姚兰的指间发出,充斥了整个房间。舒缓轻柔的音符阵阵跳动在空气中,如清风吹拂大地,又如夜晚的星辰闪烁点点星光,那不断推进和婉转的旋律,如火焰跳动,如大海的碧波,如流动的沙丘,如羊群奔跑在绿色的原野上,如鸟儿在幽静的森林里歌唱。至纯至真的幻想带着飘飞的思绪和无尽的相思与向往,冲破圈锁自由的牢笼,冲上云霄,展翅高飞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上,毫无世俗的杂念和斑点,只有天真和纯洁,只有质朴和阳光,在那圣
洁的涌动中,天空似乎越来越明亮,所有的黑暗都消失在那灿烂的光芒之中。
披头傻了,他被震撼了,他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在姚兰循环往复的弹奏中,他似乎忘记了自己。那从来不曾有过的感受,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飘送过来,从一个天真少女的手指间传递出来,像是送来一镞镞利箭,汹涌澎湃地穿透他的胸膛。他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少女起伏舒缓弹奏琴键的姿态,他被音乐,被纯朴少女舞动的身姿所惊愕,他从没有经历过这样令他无法置信的场景,那个在他眼里毫不起眼的女孩所散发的美丽圣洁的气息让他窒息。他在那一刻对女孩的看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她充满无比的敬佩和崇拜。
姚兰弹完了,她转过身,惊讶地发现对面的男孩眼眶中充满了泪水,光彩熠熠,脸膛透出平静和微笑,他呆呆地看着自己,像是傻了一样。
“你怎么了?”姚兰好奇地问。
“没什么——”披头被姚兰唤醒。他难为情地摇摇头,对自己的失态感到不好意思。“你弹得真好!让我想起往事。”
“往事?是什么?”
“我想起我的童年。”
“哦!”姚兰点点头,“是不是让你想起伤心事?”
“不,你的琴声让我想起我童年那些好日子。”
“你童年过得很幸福?”
“是啊!很幸福。”披头喃喃地说。
“那你——怎么现在会——”姚兰犹犹豫豫地问。
“你是想问我现在为什么会混得这么惨是吧!”披头突然恢复以往冷冷的神情,“实话告诉你,我没有你这么个好爸爸。”
“好爸爸——你爸爸对你不好吗?”
“好!我爸很疼我,但你要知道,仅有爱是不够的。还要有这个——”披头用手指搓了搓,表示钞票的意思。
“那你母亲呢?”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瞎打听会让你招祸的。”
“谁是小孩子!你比我大不了多少。”
“切!你懂什么?你们这些学生蛋蛋除了学习些没用的知识还能干什么。我最看不起你们这些没吃过苦还自以为了不起的大学生了,你们其实对社会狗屁都不懂。”
“那你可说错了!”姚兰回敬对面男孩挑衅的语言,“你怎么知道我们没吃过苦?你以为考大学容易吗?你有过寒窗苦读的滋味吗?我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没有你那么早接触社会,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我们自己看待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再说我们也经常参加社会活动。”
“我不想和你争!”披头傲慢地说,“和你这种大学生争没意思,你们所接触的社会都是好好好的东西。可你知道吗?江湖险恶,像你这样的学生十有八九被骗子卖了还自以为在给社会做贡献呢。”
“骗我?”姚兰轻蔑地斜眼看着披头,“我就不信骗子能骗我。你以为我是傻子啊!”
“我看你和傻子差不多。”
“你——”姚兰满脸愠色地看着披头,顿时没话了。
“算了,我也不贬低你了。看你给我弹琴的份上,我向你道歉。你还是把书念好吧,虽然我披头看不起大学生,但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国家的发达就看你们的了。”
姚兰见披头向自己认错,也恢复了平静。她说:“我觉得你——怎么说呢,其实你人并不坏,心眼儿挺好的。干吗要学坏?”
“你说什么?”披头脸色沉了下来,“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你以为我这样就是坏?告诉你,你听好了,我披头就做不了好人,在我眼里,你们的好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别给我上德育课,中学老师上得多了,我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我不是给你上课!”
“那你是什么?我可告诉你,我压根儿就没想做好人,我就这烂命,我也没你头脑那么聪明,这个社会有你这样的好人,也就要有我这样的坏人,否则怎么显得你们好呢?”
“我觉得你并不笨,其实你挺聪明的,你说话条理清晰。尽管你说的道理不对,但却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你该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
“我还有价值吗?我想我活不过三十岁。我的人生早在我爹妈抛弃我之后就注定了。”
“我知道你小时候命没我好,但你要知道每个人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却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姚兰激动地说。
“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披头用讥笑的口吻冲着天花板说,“我还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我有得选择吗?当然,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好家庭,好爸爸,我可能会比你还优秀。”
“我有很多同学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家庭很苦,但却积极向上,学习很好,很有追求。”
“对!我知道。大学里是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我也知道他们家庭条件不好。但又怎么样?至少他们父母双全吧。可我呢?我是个孤儿,我以前还有爷爷奶奶,但现在,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自己,我没有一个亲人。”
“这样——”姚兰长出了口气,她眼睛开始湿润了。感觉到对面桀骜不驯的男孩身上散发出来的悲苦的气息,她开始真正同情起这个命运凄惨的异性。
“对不起!”姚兰用温柔歉意的语调说,“我不知道你的亲人都不在了。”
“没关系!我早已经无所谓了,麻木了。说实在的,我的眼泪早已经流干了。其实,我很久没流眼泪了,刚才你的琴声让我破了戒,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不会被什么感动了。”
“我看到你的眼眶湿了。我很惊讶我能让你感动,很多人听过我弹这首曲子,但从没人像你这样过,大家只是对说我一些客气话。”
披头微笑起来,“这就说明我不懂音乐,听这曲子应该不哭才对!”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只有你听懂了。其他人仅仅是敷衍我而已。”
“是吗?我不明白——也许我适合欣赏音乐。”披头调侃地说。
“你不仅适合,如果你小时候能练钢琴的话,一定比我弹得好。”
“为什么?”
“你看你的手,手指细细长长,是弹钢琴的手。”
披头把手放在眼前,有生以来头一回认真看自己的双手,他笑了,“我这手能弹钢琴?我觉得我的手拿菜刀砍人要更合适些。”
智慧的弟弟
第10楼2007/08/12
两个月后,姚兰三哥的判决下来了,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三年劳教。三哥被宣判后与姚兰和父母见了一面,三哥哭了,他这次真后悔了,他也从心底里知道了父母是爱他的。最后他叮嘱姚兰要好好照顾父母。姚兰母亲哭了,父亲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他感觉让自己的孩子坐三年牢还是值得的,让浪子回头毕竟比什么都重要。
在探监回去的路上,姚兰的父亲在车里长吁短叹,对自己的小儿子的命运感慨起来:“
人啊!吃点苦是好事啊!”
“爸,你说我三哥在监狱里会不会有人欺负他呀?”姚兰问。
“我想不会,我托了熟人让看管在里面多照顾他。他现在和一些经济犯关在一起,那些人基本都没什么暴力倾向,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哦!爸,你说三哥有没有减刑的可能。”
“那就看他的表现了,只不过我倒想让他在里面好好磨炼磨炼。让他懂得什么是苦。”
姚兰母亲一句话不说,只在一边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