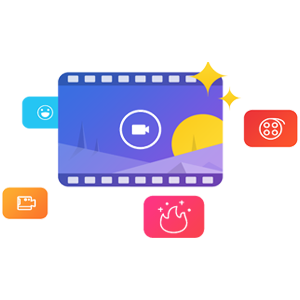

阿迈
第1楼2011/04/22
看到C章(欧洲)和D章(美洲)较大的篇幅,读者可能会指责说这就是一本声称着眼全球的著作中,明显存在西方偏见的例证。但是实际上是因为西方的食物与饮食习惯比其他地方的得到过更多系统性研究,于是这一领域也就拥有更多专业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章中负责各地区的作者都是由史前时代开始,带领读者了解各个特定地理区域的新石器(农业)革命,并关注随后由气候和文化交流所引起的饮食文化的变迁,此外还介绍了新的食物。后者最初是从中东和近东流入欧洲的蔬菜水果,以及一场早期的香料贸易,把各种亚洲、非洲与近东特产带到地中海的西缘。而罗马帝国的扩张则将上述的食物与香料传遍欧洲。
不用说,对于1492年之后,在旧世界各国与新世界各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动植物交流,本书描述得相当详细,因为这些交流深刻地影响了所有这些地方的食物(以及人口)历史。当然了,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美洲人已经在他们自己历时数千年的新石器革命中驯化和传播了玉米、木薯、红薯、土豆、花生、西红柿、辣椒以及一系列豆类,并以之维生。不过这样的美洲食谱中缺乏动物蛋白质。仅有的一点动物蛋白来源于猎物、豚鼠、水产、昆虫、狗和火鸡,因地理位置而异。美洲印第安人为什么不驯化更多动物——以及为什么不从他们驯化的动物(例如美洲驼)身上挤奶——仍然算是个谜。比较没有悬念的是美洲土著人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一场欧洲人无意中利用疾病发动的大屠杀。而这片新领地上的人口减少了之后,又布满了马、牛、羊、猪等等来自旧大陆的牲畜。
新世界的植物食品配上旧世界的动物食品,自是金玉良缘,而当负责各个地域的作者行笔至当代——实际上是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一个重要的主题从字里行间浮现,那就是在食物全球化的强大力量面前,独特的地方风味渐渐消逝。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烹饪风格,正在同质化,甚至是太平洋,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多地食用西方式的加工食品,不幸的是这对他们有害无益。
阿迈
第2楼2011/04/22
E章用三节篇幅记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太平洋岛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饮食文化,就此完成了一场环球美食之旅。尽管乍看上去这三地历史上毫无瓜葛,从营养学角度来看也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实际上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比较缺乏可食用的动植物物种。
在非洲,这种缺乏主要应归咎于降雨量,在不同地域,总是过少或者过多。前者酿成灾荒,后者则带来淋溶作用,造成土壤中氮和钙的流失,因而当地的作物也就缺乏重要营养物质。此外,40英寸以上的降雨有利于采采蝇的繁衍扩张,这种昆虫所携带的致命锥虫造成非洲许多地方无法蓄养牲畜。即使能养活,用作饲料的植物也缺少营养,造成牲畜个体大小以及产肉产奶的质量都不如世界其他地方。与南北美洲的情况类似,定居农业时代到来后,多数非洲人的日常饮食并不以动物蛋白为主。
可是非洲不像南北美洲那样,在植物食品方面那么得天独厚。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小米、薯蓣以及一种非洲大米,聊以养活本地人口,在一种比较高产的薯蓣品种横渡印度洋而来之后,人口进一步增加了。但是只有等到奴隶贸易带来的玉米、花生、甘薯、美洲薯蓣、木薯和辣椒传入,非洲人口才开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飞速增长。
大约三万至四万年前,太平洋先民开始从东南亚一波波扩散,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他们过着一种渔猎采集的生活,食用各种鱼类,鸟类以及爬行动物,还有蕨类的根和其他野生蔬菜。但是一批较晚的移民,在约六千年前从东南亚渡海迁移到太平洋岛屿上时准备更充分,他们带上了猪、狗、鸡以及薯蓣和芋头之类块根作物,这都是旧世界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成果。而很久以后,一种美洲作物——甘薯——以某种方式传遍了大部分岛屿。
阿迈
第3楼2011/04/22
所以说,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实际上是“进口”来的。不用说这个传播进程会很慢,但是到了库克船长驶入太平洋的时候,所有有人类定居的岛屿也都拥有了猪、狗和家禽——甚至包括最与世隔绝的夏威夷群岛。然而,当欧洲人送来动植物新品种的时候,太平洋岛屿原住民与美洲原住民一样无福享用。他们很快就染上输入的致命疾病,人口骤减。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况与非洲和太平洋岛屿截然不同,最初与欧洲人接触时,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西兰毛利人都还是狩猎采集者(后者不完全是)。他们既没有猪和家禽,也不种薯蓣和芋头,只有一种中等身材的狗,还有甘薯。
新西兰在人类到来之前是没有陆生哺乳动物的,不过有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和大量爬行动物。毛利人自波利尼西亚出发前往新西兰时,波利尼西亚已经有了猪和芋头,可是他们在某个时点(或许是在前往新西兰的路上,或许是到达之后)失去了猪,而且新西兰的土壤和气候不利于芋头的生长。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相似,他们也保留了狗,有时也把狗当作食物,甘薯是他们最重要的作物。
于是,除了养狗和一些种植的努力外,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毛利人非常倚重狩猎采集活动,直到欧洲人带来新的动植物物种。不幸的是,正如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其他地方一样,他们还带来了新的病原体,结果自然还是人口锐减。
在环球游历之后,第五篇以一章对烹饪历史的讨论作为结尾,这一领域目前在欧美蓬勃发展,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有全世界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讨论。
阿迈
第4楼2011/04/22
第六篇专注于食物与营养相关的课题,涵盖了当代与历史上各个时期。其中有人类以惊人的适应力应对各种特殊营养条件的实例,包括因纽特人的奇异食谱,他们高脂肪的传统饮食足以堵塞动脉,却平安无事地一直生存到如今,令研究者大惑不解。其他章节继续讨论各种特殊时代、经济体和族群的营养需求(以及权利)问题。它们显示了这些需求如何频繁地因文化和经济条件所限而难以满足,并指出母婴营养不足的后果,诸如智力退化等,正在得到详细的研究。在同一主题下,我们也讨论了食物偏见与禁忌;这类行为多数会给妇女儿童带来严重的营养问题,况且生育基本上就是一项营养工作,而长大成人更是一场营养的长征。
对于饥荒的政治、经济和生物原因及影响的讨论,引出了另一个大问题,第六篇的前两章就针对于此。自从Thomas McKeown在1976年出版《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之后,营养在人口历史中的重要性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在这本书中McKeown试图解释:至迟在十八世纪时,英国人——同理可以外推到欧洲人——是怎样成功地跳出人口的“先增长再停滞”这一怪圈的。在排除了医药及卫生的进步,以及疾病弱化或突变等流行病学因素之后,他认为营养改善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用说,如此武断地排除其他选项自然会激起争议,我们还会在其余章节中讨论到一些相反的主张。
与本篇内容相关的还有身高和营养条件的讨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一个指标。显然,无论营养改善是不是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它都必然在人体发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绝非偶然地帮助了(至少是居住在西方的)人类身高恢复到了他们新石器时代远祖曾达到过的高度。此外,不管人们对于营养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持何态度,至少都能达成共识——营养与疾病脱不了干系;而我们正有一章专门讨论两者的相互作用。
接下来的章节关注食物的文化和心理学属性,研究人们取舍不同食物的原因,以及与这种食物好恶密切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时下,食物取舍常常成为时尚主题,所以有一章专门讨论造成某种食物忽然流行,又往往迅速失宠的许多原因。
本书用观点截然不同的两章体现了素食主义的争议性——这个话题永远能招来辩论火力。有人把素食归入食疗领域;有人则相信素食的壮阳功能——认为回避动物食品可以促进性欲和机能;有许多人出于宗教信念而吃素;又有些人就是觉得杀生吃肉不对,还有人认为食肉根本就是危险行为。显然,“吃啥长啥”这句话各人都有各自的理解。
阿迈
第6楼2011/04/22
第七篇主要内容是详细探究了食物相关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在从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过第一章先以营养与国家的关系为起始,揭示欧洲国家如何逐渐地把人口营养条件与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联系起来。接下来的论题有:在确定个人每日主要营养成分最佳摄取量时,所遭遇的无数方法论问题(生物学问题就更不用说了);食物标签的实施问题,如果做到公开公正,则有助于个人作出正确选择以满足营养需要;以及对于非食品补充饮食的效果的质疑。
不出人们的意料,食品安全,食品生物技术以及相关政治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密切关注,而且自然而然的,政治与安全总是步调不一致。这对冤家并非新近结成的,其中一方背后有垄断竞争的资本力量,另一方则代表公众利益。两者并不总是背道而驰,但我们即将看到,二者的关系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是安全问题,由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引起。因为所有的作物都是自野生品种演化而来,这意味着,用达尔文主义的说法就是,野生品种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了生存所需的适应能力。然而在驯化与种植中,发生了遗传侵蚀,这种适应力也遭受损失,甚至其野生祖先也可能灭绝;于是今天的很多作物一旦突然间无人种植,直接就会消亡。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怎么吓人——毕竟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停止种植小麦、大米或者玉米——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了很多遗传特质,我们所种植的这些作物的遗传多样性非常贫乏,并已引发了相当的重视;因为一旦出现某种突变的植物瘟疫,打击了世界粮食供应的相当部分的话,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还有一个问题与遗传多样性的缺损有关。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相对不那么严重,不过人们并不能因而高枕无忧,尤其是长期的危险性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许多作物已经不太能抵御传统的寄生虫(部分原因是培育过程降低了植物自身产生毒素以防御天敌的能力),因而越来越依赖农药,为农药侵入我们的食物和饮水大开方便之门。
基因工程则号称能够反其道而行,唤醒作物的抵抗力以降低化学污染的危害——例如,把食肉植物与土豆进行杂交,这样落在上面的昆虫就会立刻死掉。可是这种对于植物防御机制的激励也引来了忧虑,因为人吃植物,所以对植物而言人类也是天敌,抵抗力基因有可能使作物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人体健康,如果一旦达到致癌的程度(如前文所述)则更是令人无法接受。同时,基因工程自然更引起这样的恐惧,担心科学家无意中(或故意)制造并释放出自发繁殖的微生物到生物圈中造成瘟疫或生态灾难。
显然,生物科技,植物育种,植物分子和细胞生物学以及农药产业都是前景与风险并存,本书关于食物中毒物的一章就描述了其中一部分风险。而且作为补充说明,关于替代食品的下一章显示,尽管这些代用品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糖和脂肪的统治,但它们自身也并非完美。同样,有一些食物添加剂也不安全。而诸如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之类的防腐剂,味精之类的增味剂,以及柠檬黄之类的着色剂即使多数都是安全的,也仍然使许多人忧心忡忡。
但是,我们的作者明确指出,与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相比,其危险性还不如所谓的自然食物中带有的自卫性质的毒素,后者更值得人们操心。例如芹菜含有补骨脂素(原文作psoralin,wikipedia作Psoralen或Psoralene,是诱变致癌物质);菠菜含有草酸,会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并引发肾结石;利马豆含有氰化物;而发绿的土豆皮中含有的茄碱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
接下来我们从生物和化学问题转到与政治经济关系更密切的课题上来,诸如生产哪些食物,产量多少,质量要求如何,以及如何分配。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地方),这些政策是由游说团体协商决定的,而他们只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不能代表公众。不过好在即使美国人有时在了解自己吃到的食物上面会遇到障碍,但至少他们还有的吃。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一种大致的(哪怕有点不太情愿的)共识:获得食物是一项基本人权,而政府应该设法通过补贴、食物券等手段来保证这项权利。 但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就还做不到,那里无钱无势的人常常得不到救济。而本书关于食物补贴与干预一章的作者明确指出,太多的妇女儿童属于无钱无势的人群。
最后,与本书的开端相呼应,第七篇讨论了新石器时代形成的营养模式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重要性,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又引人入胜的问题,也为本书留下一个较为轻松的结尾。
阿迈
第7楼2011/04/22
我们以夹杂着乐观与悲观的复杂感情结束这篇绪论。我们给现代作物品种加入矮杆基因,培育出非常高产的小麦和大米品种,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广,终于促成了所谓“绿色革命”,人们原本希望这能消灭饥荒并帮助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现粮食富余。然而绿色革命同时也在其影响到的国家中触发了一场巨大的人口爆炸,造成马尔萨斯所说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的发展极同时出现。
更有甚者,庄稼新品种极度依赖于石化工业生产的化肥,于是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油价暴涨时,化肥价格随之上涨,造成原先依靠土地收成勉强糊口的穷苦农民破产而失去土地,背井离乡。而新培育的矮杆和半矮杆水稻和小麦携带着相同的基因,意味着全世界大部分的粮食供应在新出现或新变异的植物病原体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更糟糕的是,这些作物似乎连抵抗现有病原体的能力也不足。应对之道似乎只有更加大肆施用农药(环保人士则强烈反对),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承受不起高涨的成本而被逐出农业;而饥荒还在年年肆虐,夺去万千生命。实际上,每一个原指望依靠绿色革命达到粮食富足的国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都再次沦为粮食进口国。
显然,无论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角度看,生态不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被严重破坏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关于水稻和小麦的章节中所指出的,育种者已经得到携带有能使作物不受流行病伤害的突变基因的新品种,而以培育出不依赖化肥和农药的品种为目标的基因工程努力也有所进展。
同时,本书其他的作者也指出,如果人类集中在大米和小麦上的精力能够分配一些给诸如苋菜,甘薯,木薯和芋头之类的食品,则可以大大扩展世界粮食供应。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再次遭遇食物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属性与生态和生物学属性孰轻孰重的难题。这些问题无疑将会影响到人类对高营养新作物的接受程度。
正当一场第二次绿色革命应运而生之时,观察家希望我们能够从第一次革命中吸取教训。不过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看作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研究自那时以来的所有教训——概括起来就是迄今为止的每一次重大的农业突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总是使卷入其中的人健康更差,而总体的农业进步则造成人口增长,给生物圈带来严重压力。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我们的希望仍然在于,要能真正从人类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